父親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,不善表達。我們姐弟七個,加上我們的孩子,有二十多口人,使我們一大家人融洽相處的是母親。四年前,母親去世后,父親一個人住。耄耋之年的他,身體每況愈下,給他雇了保姆,四年換了三個。臨近春節,保姆又借故離開了,我們姐弟輪流照顧他。
晚上,我在父親隔壁房間,往事浮上心頭。母親在世時,兄弟姐妹經常聚在這里聊天說笑,現在剩下他一人,冷冷清清,我們來看他時,他大多坐在電視前藤椅上,面前桌上擺滿他平時要吃的各種藥,孤孤單單的畫面讓我們傷感不已。父親在等待生命的落幕。
冬天早晨,寒冷逼人。早上醒來,去洗漱,看到廚房里父親坐在那里的背影。我問:“爸,你起來那么早干嘛?”他說:“我在熬粥,你早上上班要吃早飯。”父親笨拙的身體,走出廚房,又挪動著碎步去冰箱拿饅頭,然后緩緩又回到廚房,在灶頭上蒸起饅頭,他雙手插在袖籠里,依然靜靜坐著。
父親這幾年老得很快,腰像蝦米,走起路來,好像在地上挪動。他的手干枯,黑且瘦,像一根蠟染的枯枝。我的眼淚止不住涌出眼眶,父親自己已是風燭殘年,卻依然像過去那樣照顧子女,幾十年來,默默付出了全部心血。
十二歲那年,我小學畢業考試。那時,語文、數學達不到及格分,是上不了中學的。父親當時是我那所小學副校長。我的成績一直在班里倒數,父親卻從來沒有因為我的不爭氣而批評過我。直到五年級,我才稍稍努力。拿畢業成績單那天,我看見父親遠遠從村頭騎著自行車回來,他微笑著告訴我:“還不錯,都及格了。”那時,我并不理解父親笑的含義,那是他用無聲的語言表達對女兒進步的欣慰吧。
弟弟的出生,讓父親丟了校長的職務,只能在學區做會計。上世紀九十年代,正趕上“撤區并鄉”,父親連學區的會計也丟了。后來,姐姐們相繼出嫁,農活沒人干,父親不得不攜我們舉家搬遷至鎮上。那是一段灰暗的時光,父親的基本工資根本養活不了一大家子,他先后販賣過毛竹、食鹽。過多的體力透支,讓他患上腰痛病,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月。為了全家的生計,他還是支撐著去進貨賣貨,一瘸一拐的身影留在少年的我的印象里。
也正是艱苦的環境,讓我上中學時,異常刻苦。中考時,我考了全校第一名。分數下來那天,父親去給我查分數,依然騎著那輛自行車,一直騎到我家房屋的中央才下來,他說:“考了430分!”他微黑的臉龐露出少見的笑容,雙眼透露著慈祥的光。當時的我,是多么想聽到他的表揚啊,可是他除了笑了笑,就悶不作聲去做他自己的事情了。后來,從母親口中得知,父親因為我考得好,興奮得一夜未合眼,天沒亮就起來去親戚家借錢,給我做學費。
十九歲的我中師畢業,在縣城一所小學工作一年后,又考取淮南師范學院脫產進修。那一年,父親因為會計工作做得出色,被鄉鎮教育辦公室調去做了教育干事。我去上學的第一天,父親讓單位的司機送我去學校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,小轎車在普通家庭還是稀有品。開學那天,父親帶的轎車,讓我在同學面前長了一次臉。開學不久,父親又親自來學校一次。中午,我帶父親在學院飯館吃飯,他寥寥數語說了弟弟學習上的事,默默吃飯。臨走時,額外給我幾百元生活費,當時我是帶薪學習,每個月工資完全花不掉。后來,我放寒假回家,母親告訴我,父親說一個寢室的女孩都沒有他家丫頭長得好看。
父親是陪著我們長大的人,而我們卻不能陪著他老去。每當回想起與父親的點點滴滴,心中總會有一股莫名溫暖,一種無法言喻的溫馨。父親用他默默無聞的一生,支撐著整個家庭,為子女,他操勞、吃苦、節儉……
人總是有意無意忘記時間的殘酷,忘了歲月的無情和生命的脆弱。有的遺憾可以彌補,有的失去了就無法重來。許多時候,因為事業、家庭,瑣碎的事務壓得我們難以喘口氣,我們有太多的理由去忽略他、冷落他。雖然子女多,而年老的他卻只能孑然一身,除了物質上的給予,年老的父親更需要子女的陪伴。哪怕再忙,一個千里之外的電話問候,陪伴左右的促膝談心,小小心愿的滿足,都是對父親極大的精神慰藉。
(汪秀麗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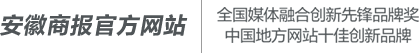
 設為首頁
設為首頁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系我們
聯系我們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