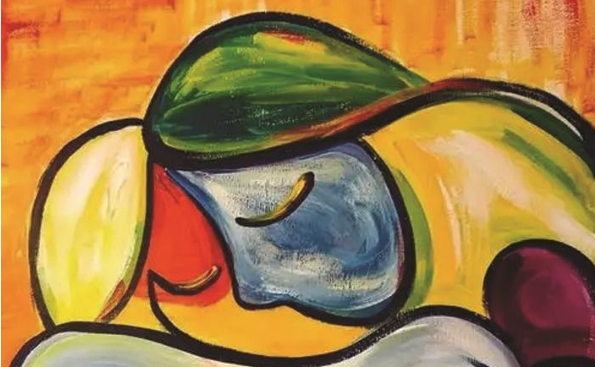人間處暑秋
□楊麗麗
處暑的風是帶了秤的,稱走了伏天最后一絲黏膩,秤桿一翹,漏下的全是清清爽爽的涼。晨起一件外套,袖口掃過桌面時,帶起一陣風,有了清冽的意思。
案頭的茉莉開得正好,卻也透著點見好就收的懂事。花瓣不再是伏天里那種水潤潤的白,多了層霧狀的粉,像敷了層薄紗。香氣也淡了,若有若無地繞著鼻尖,不像大暑時那樣霸道,非要鉆進人心里不可。
街上的人換了衣裳。姑娘們的裙擺長了些,料子也厚了,走起路來沙沙響,像秋草在風里低語。街角的桂樹,枝丫間藏著小小花苞,像撒了把碎米,湊近了聞,已有淡香,不似茉莉那般躲躲藏藏,倒帶著點篤定。
去公園散步,兩個老人打太極。招式慢悠悠的,抬手、落掌,都帶著股從容不迫的勁兒,倒比盛夏時那些跳廣場舞的熱鬧,更合了這節氣的脾性。銀杏葉還綠著,卻比往日硬挺了些,邊緣泛著淺黃,像被誰用金粉描了邊。長椅上落了片葉子,拾起來看,脈絡清晰得像老人手上的青筋,藏著一整個夏天的故事。
湖邊的蘆葦開始抽白,毛茸茸的穗子在風里晃。水比夏天淺了半尺,能看見水底的卵石,附在上面的青苔也瘦了,不像伏天那樣綠得發膩。我往水里扔了塊土疙瘩,驚起兩只蜻蜓,一只是紅的,一只是黃的,飛得都比夏天慢了,翅膀扇動的聲音也沉,像馱著什么東西。
沿著湖岸往前走,撞見幾個孩子蹲在石階上,手里捏著網兜,正盯著水面上的浮萍。往日里瘋跑著追蝴蝶的勁頭收了些,說話都放輕了聲,怕驚了水里游得慢悠悠的魚。有個扎羊角辮的小姑娘,手里攥著片梧桐葉,她忽然抬頭問:“奶奶,葉子是不是在攢力氣,等天冷了就變紅呀?”
風從湖面卷過來,帶著點水腥氣,卻不黏人了。岸邊的垂柳把綠裙子收短了些,枝條不再像盛夏時那樣沉甸甸地垂到水里,倒像梳過的頭發,輕輕巧巧地晃。有老人坐在石凳上,手里搖著蒲扇,卻不怎么扇了,就那么有一下沒一下地晃著,扇面上的荷花圖案褪了色,倒和這秋意里的清淡合了拍。
菜市里倒熱鬧,只是少了些聒噪。賣秋茄的攤前,茄子紫得發暗,帶著層薄薄的白霜,像蒙了層霧。攤主是個穿了件長袖藍布衫的胖嬸,笑著招呼客人:“這茄子再不吃就老了,秋后的菜,一天一個模樣。”旁邊鼓鼓的毛豆堆得冒了尖,剝開一個,豆粒圓滾滾的,帶著股清甜味,不像夏天的豆子,總帶著點生澀。
路邊野菊開了零星幾朵,黃燦燦的,藏在草叢里,不像春天的花那樣招搖,倒像攢了一整個夏天的勁兒,就等著這陣涼風吹過,慢慢把顏色鋪開。有只麻雀落在電線上,歪著頭梳羽毛,梳著梳著,忽然撲棱棱飛走了,翅膀帶起的風,吹得旁邊的狗尾巴草晃了晃,穗子上的絨毛,沾了點陽光的金。
想起昨夜的月亮,比夏夜的清瘦些,掛在天上,像誰晾在竹竿上的銀鐮,把最后一點暑氣割得干干凈凈。窗臺上的仙人掌,尖上冒出點新綠,硬挺挺的,倒比夏天時精神。原來秋不是一下子來的,是風一點點稱走了熱,是葉一片片攢起了黃,是日子在晨露和夕陽里,慢慢換了件清清爽爽的衣裳。
吃新豆
□米麗宏
八月,豆田青郁郁。豆棵半人高,父親進田看豆莢長勢,一俯身,背影就融在了綠里,斗笠像一個金黃的圓漂浮著。
這塊黃豆地,第一次來看是“五一”假期,那時星星點點的“丫”字,著鵝黃淡綠的童衫,橫成行豎成列,像小學生做廣播體操。第二次來是端午,豆苗兒已嘩然齊膝,葉子毛茸茸攢滿地壟,綠水漫灌不見地皮。豆花也開得撲棱有聲:粉白的,花朵上沾著粉粒子,一摸膩手;白里透紫的,素雅而神秘。白的紫的搭伙兒開,像繁星降落碧海,閃閃爍爍,搖搖曳曳,讓人心喜。
如今再來,已是萬棵掛莢,一簇簇豆莢團在豆棵胯部,擁擠著,熙攘著。青青豆莢,珠胎暗結,像懷孕的豆媽。莢皮被豆粒撐得鼓脹脹,一顆一顆,硬挺飽滿,好像憋著一股勁兒;剝開豆莢,豆粒青青的色澤,潤潤的手感。拿到鼻子底下一嗅,一縷清鮮的豆腥氣,清甜純凈;放口里品品,淡淡的草甜,輕輕的豆腥,如此時剛剛起步的秋風,輕盈,細嫩,又軟又萌。
處暑,正是吃鮮豆的季節。父親讓我們采一籃子,回家蒸豆。放點鹽,鍋里一壓,軟軟糯糯,香香甜甜,那是毛豆嗎?那是節令的嫩汁、八月的時鮮呀。
毛豆這東西,不僅不挑地,還肥地。植株上那些根瘤,就像一個個造肥場。再瘠薄的地,種一季黃豆,好了,往下種啥長啥,黃豆替你養地了。
村子里,紅白喜事和年節的豆腐,乃至豆油、豆漿、豆汁、豆皮、豆醬、豆芽、豆腐腦,哪個缺得了黃豆哇?看眼下這黃豆的長勢,收獲也不過一個月的光景。等它們再蓄蓄粉,收收水,葉也卷了,莢也干了,籽也硬了,秸稈兒木質化了,隔莢皮可看出豆粒兒的肥瘦了,好,那時節我們再來幫父親割黃豆。
我們再去楊樹灣的綠豆地摘一籃綠豆。地只有一分,每年產下的豆子,足以供應我們姐弟三家一年食用……等豆罐見底兒,新一季綠豆又莢黑粒兒滿了。
綠豆的綠,很迷人,亮,純,明艷,像采集了天地之光的那種幽邃的綠。有一種牡丹叫“豆綠”,那是華美貴族對民間之美的追慕。牡丹和綠豆,綠得真像,也都美。
櫥柜里有一個灰藍色土制的瓦盆,常用它生豆芽。清水泡胖綠豆,看它努出尖尖嘴兒,就挪到能吸水也能瀝水的瓦盆。濕布覆蓋,一天淋一次水。三五天,豆芽暄蓬蓬拱出了盆沿兒。抓一把豆芽和著紅辣子爆炒,或者過水拌涼菜,那天然的豆香、脆脆的口感,每每吃得欲罷不能。
有句俗話:豆芽到老一根菜。是說它混得人緣和光景都夠嗆?我還挺喜歡這種喧囂中的冷靜獨立呢。綠豆,芽嫩綠,葉翠綠,花兒黃綠,籽粒呢,幽綠。綠豆做糕做湯,是或深或淺的綠。這種叫“綠”的豆子,真是把“綠”鋪排到了生命的每一個細節。
眼前的地里,綠豆長得隨性,植株下部結著莢,有的莢黑了,有的還綠著;植株上部開著花,花兒明明黃黃的。這樣的情形總是讓人躊躇,割呢,它還有莢在生長;不割呢,有的豆子已長成,一性急,就會莢皮爆裂,豆子像微型導彈一樣發射到遠處。
這是處暑的美好,新秋的饋贈,我們總會充滿新奇地去接受時令的美意,一年一度,從不缺席。
把夏與秋縫在一起
□白麗霞
絲瓜藤在晾衣繩上打了個結,把最后一朵嫩黃的花垂在晾著的藍布衫前。母親正翻曬竹匾里的芝麻粒,她抬手抹汗時,腕上銀鐲子碰響竹匾,驚飛了檐下啄食的麻雀,這便是處暑了。
處暑的晨露總比往日重些,沾在豆角藤上,像誰撒了把碎鉆。鄰家李嬸挎著竹籃摘秋葵,褲腳掃過草葉,帶起一串晶瑩的水珠,落在青磚地上洇出淺痕。“這天說涼就涼了。”她對著蹲在籬笆邊看螞蟻搬家的我笑,“前兒個還熱得直扇扇子,今早就得套件薄褂子。”我伸手撿起一片梧桐葉,葉脈上還掛著露水,湊到鼻尖一聞,竟有股清甜的草木氣。
午后的陽光斜斜地穿過堂屋,在八仙桌上投下窗欞的影子。奶奶坐在竹椅上剝蓮子,竹籃里堆著青褐色的蓮蓬,剝開時露出乳白的蓮子,蓮心是嫩黃的。“吃些蓮心敗敗火。”她把剝好的蓮子塞進我的嘴里,自己卻把蓮心都收進小瓷瓶,“留著泡茶,秋燥的時候喝正好。”
村口的老槐樹下聚著些納涼的老人,手里搖著蒲扇,扇面上印著“春耕夏耘”的字樣。李叔叔的煙袋鍋子“吧嗒吧嗒”響,說:“今早去田里看稻子,稻穗已經沉甸甸地彎了腰,再有個把月就能割了。”王嬸手里擇著豇豆,豇豆是紫皮的,擇下來放進竹筐,紫瑩瑩的一串,像誰串起的瑪瑙。遠處的稻田里,稻草人戴著草帽,衣角被風吹得獵獵響,驚走了偷食的麻雀,卻驚不醒趴在稻草人腳下打盹的老黃狗。
傍晚的霞光格外柔和,把天邊的云染成淡粉。孩童們在曬谷場上追逐,踢起的谷粒在空中劃出金黃的弧線,落在草垛上,驚起幾只螞蚱。母親站在灶臺前烙餅,面團在案板上“咚咚”響,鏊子上的餅鼓起金黃的泡,香氣混著院里桂花的甜香飄出老遠。父親扛著鋤頭從田里回來,褲腳沾著泥土,進門就喊渴,母親遞過一碗晾好的綠豆湯,綠豆湯里漂著顆蜜棗,喝下去,從喉嚨涼到心里。
月亮升起來時,蛙鳴已經稀了。院墻邊的蟋蟀開始唱歌,聲音清脆,像誰在彈撥琴弦。奶奶搬張竹床放在院里,鋪上曬干的稻草,躺上去沙沙作響。窗外的老棗樹上,最后幾顆紅棗在月光下閃著紅光,像遺落在枝頭的紅瑪瑙。遠處傳來幾聲犬吠,接著又歸于寂靜,只有蟋蟀的歌聲在夜色里流淌,伴著漸起的秋意,漫過村莊的每一個角落。
這便是處暑了,像奶奶納鞋底時穿過的線,不緊不慢地把夏與秋縫在了一起。熱還在,卻添了幾分收斂;涼已來,又帶著幾分溫柔,就像灶臺上溫著的米酒,余溫里藏著醉人的甜。
草蟲吟
□劉建峰
處暑的日頭是收了性子的。先前總把柏油路曬得冒白煙,如今斜斜地照在院墻上,倒像摻了水的蜜,稠是稠,卻少了灼人的烈。門樓下的竹床被祖父搬進堂屋,說“過了處暑,夜涼浸骨頭,潮氣傷身體”。
風也換了脾氣,不再卷著熱浪撲人臉,摸上去是溫吞的,像祖母剛晾好的米湯。到了黃昏,這風忽然就停歇了,連墻根那叢牛筋草都支棱著葉片,一動不動,似乎在等什么。
蟬鳴早幾日就稀少了。先前整樹整樹的“知了——知了——”,吵得人午覺都睡不安穩,如今只剩零星幾只,嗓子也啞了,“知——了——”拖得老長,尾音里帶著點顫抖,像漏了風的風箱。它們是熬不過處暑的,祖父說,“伏天的蟲,火里生。處暑的蟲,土里藏”,話剛落音,最后一聲蟬鳴便斷在暮色里,世界猛地安靜下來。
這靜,是給蟲兒們騰的場子。
頭一聲從柴草垛里鉆出來,細溜溜的,“吱——”,像誰用針尖挑破了秋夜的薄紙。停頓片刻,西墻角的磚縫里應了一聲,更沉些,帶著點沙礫感,像石碾子碾過干硬的土塊。跟著,菜畦邊的豆角架下、葡萄藤的老根旁、堆著南瓜的草筐底,數不清的嗓子一起亮了,蟋蟀的“瞿瞿”,蟈蟈的“聒聒”,還有些叫不出名的小蟲,發出“咝咝”的微響,纏成一團,把這處暑的夜填得滿滿當當。
祖母搬個小馬扎坐在院里,手里攥著補了補丁的蒲扇,卻不搖,就那么支著下巴聆聽。月光爬上籬笆墻時,她鬢角的白發泛出銀輝的光芒,跟草葉上剛凝的露水似的。“你聽東頭那只,”她忽然扯我的袖子,“調子發飄,定是昨夜讓露水打了。”我屏住氣,果然有只蟋蟀的聲兒忽高忽低,像踩在搖晃的草稈上,隨時要跌落下來。
葡萄藤下藏著另一種不知名的蟲子。聲音細細的,像紡車轉得飛快,“吱吱——”地繞著垂下來的青葡萄轉。葡萄粒剛有指甲蓋大,被月光照得透亮。這蟲兒不摻和別處的熱鬧,總在藤葉最密的地方哼唱,像個守著秘密的老婦人,數著粒兒過日子,一粒,兩粒,數得專心又虔誠。
露水漫過腳踝時,蟲鳴浸了水汽,聲腔也變了。先前的脆生勁兒淡了,添了層濕漉漉的黏,聽著像隔著層浸了水的棉紙。蟋蟀的聲兒沉下去,像掉在井里,嗡嗡地發悶。那紡車似的細響卻亮起來,帶著點清凌凌的涼,順著藤架爬上來,沾在胳膊上,激得人打了個輕顫。遠處的稻田里,偶有蛙鳴滾過來,被露水打濕了翅膀,落到院墻上時,只剩半截模糊的尾音,像誰在夢里含糊的囈語。
祖母起身回屋時,我跟著她往屋里走,看見月光把她的影子鋪在地上,又被門檻攔腰截斷,像幅沒畫完的水墨畫。
灶上溫著的南瓜粥該好了。揭鍋蓋時,白汽“騰”地涌出來,混著南瓜的甜香漫到院里,蟲鳴忽然就低了半拍,像是被這熱乎氣燙了嗓子。祖母盛出兩碗,撒上點桂花糖,瓷碗相碰的脆響里,蟲聲又慢慢漲起來,裹著粥香,裹著月光,裹著墻根磚縫里藏不住的秋涼。
后半夜被尿意催醒,聽見窗外的蟲鳴稀了些,卻更加清亮了,像被露水淘洗過。摸黑穿鞋時,踩在地板上的響動驚得院角一只蟋蟀戛然收聲,等我重新躺下,它才試探著“瞿”了一聲,跟著,遠處又有兩三只應和起來,零零落落。
天快亮時,起風了,帶著明顯的涼意,處暑的清晨,也裹著蟲兒們未唱完的調子,慢慢亮起來,和著遠處稻田里最后的蟲吟,把這秋的序幕,拉得又長又綿。


 設為首頁
設為首頁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系我們
聯系我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