姥姥去世之后,我媽經常獨自坐在公交車上哭。她說:也不知怎么了,眼淚止不住。就覺得委屈,不是為自己,是替姥姥委屈。
姥姥去世的前三年,住我家。那時候,家里蹲著兩個老太太。一個奶奶,一個姥姥。她們都是多子女的家庭,在老伴接連去世之后,選擇在最小的兒女家里生活。
家是平房,很小。一處小院,一個屋子,一張炕,最里面是做飯取暖的爐子。
華北平原上的平房,蓋得密密麻麻,遠看像是無數包火柴盒扔在了地上,胡同的一側是各家各戶的門,對面是狹小四方的后窗,像小時候寫字用的田字格。有一次,三姑在我們家煮玉米。夏夜里,她光膀子就跑去后廚取玉米,看見后窗上赫然有一張臉,三姑一手拎一個玉米,“嗷”一嗓子,嚇得偷窺者末路狂奔。
上世紀九十年代有段時間治安環境不佳,社會上流行著各種各樣的事。有一陣,有人會把抄寫的冊子掖到門縫里,上面赫然寫著,抄寫二十份傳遞給其他家,可保平安……于是,家里大人小孩開始抄寫,半夜偷偷出去傳遞。當時的人們,因為消息閉塞,總被某種神秘主義所裹挾。
我家平房雖小,但人數眾多。就像那種電影里的意大利家族,日常都會圍繞在老人身邊。腳前繞,身邊繞,嘰嘰喳喳的,像老母雞身邊的一群小雞。有時候,我感覺奶奶像個漢子,姥姥像個小女人,她們是兩口子,在一起搭伙過日子。
寒冬大雪。早上我去上學,看見火爐上茶壺正沸騰,旁邊是幾個花卷,烤得微微焦黃,發出“滋滋”的聲音。一邊,炕上擺上四方矮炕桌。奶奶從缸里撈出咸菜,那是用壓菜石頭壓了整整一個秋天的芥菜,切成絲后脆軟酸香。姥姥負責泡茶,一個四方的茶葉罐,罐中是湖北產的磚茶,渡千山過萬水來到了我家。會放幾個冰果在罐子中,增加香氣。
她們兩人盤腿坐在炕桌前,開始泡茶吃早飯。我背著書包,去上學。走出門后往里看了一眼,炕上熱氣彌漫,窗欞上映照著她們的笑聲。當時我想:啥時候我能過上這種日子。
下午,她們會叫上鄰居老太太,在家里打一毛、兩毛錢的麻將。她們在老頭都走掉之后,宛如姐妹,度過了一段悠閑愜意的時光。
事情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變化的?我也說不清。據我媽的回憶,姥姥是接到了兒子的通知,讓去看孫子。兒子的老婆為人跋扈,潑辣無比。給我舅舅下了死命令:叫你媽過來看孫子!
我姥姥背著一身行囊去了兒子家。在那里發生了什么事,我都不知道。直到有一天,姥姥身體不適去看醫生,是肺癌晚期。很快,三個月左右,她就走了。
離開的時候,姥姥腦子已經糊涂,半昏迷狀態。子女們商量后,決定每個人下班去陪床。偏偏在我爸媽陪床的那天,她走了。兩人站在院子中央一臉茫然,我媽去隔壁找她的舅舅。我爸一個人在屋里不敢待,躲在院子中央抽煙。
老舅舅是過來人,一進門就說,愣著干嘛,趕緊穿衣服。幾個人開始著急忙慌地穿戴,老舅舅摘取姥姥的耳環、戒指。摘到戒指時,死活摘不下來,抹了油也摘不下來。老舅舅跟我媽說:你媽一直小心眼,這是怕我拿走呢。你來摘。我媽一摘就摘下來了。
這些事,我沒有親見,都是我媽復述的。起初只當故事聽,后來只剩唏噓。
我媽說:打發你姥姥時,請了所有親戚。沒想到當天,大舅媽和二舅媽打起來了,為了爭家產。可是你姥姥根本就沒留下什么家產,她內心更覺悲傷,戒指也沒留,給了我大姨。
前期忙忙亂亂,來不及傷心。在姥姥走后幾年,她突然悲上心頭。那時我們也搬了家,住的很遠,她每天要坐一小時公交,就利用這一小時在公交車上偷偷哭。
時間又過了很多年。早年跋扈的大舅媽最后信了佛。有一次懺悔:我年輕時候太混蛋了,開過熟食鋪子,攤過煎餅,一心為賺錢,我對不起我男人……哦,還有我的婆婆……
在我從小到大的日子,看見過很多這樣的女性。像祥林嫂一樣生活,悲苦交集,逆來順受,度過自己的一生。存在過,也沒存在過。從未為自己活,日后也很少人會想起她們。她們就像大地上的野草,簇擁映照著一兩朵野花。
當時,我覺得事情就該這樣,大地假如沒有野草,那一兩朵鮮花未免也太突兀了。直到某天我看見大黑河沿岸的薰衣草園,才發現如今鮮花也可以簇擁著生活。
姥姥臨走前,一個人在炕上縫一件衣服,她說,女人么,就像這手上的頂針。家里再多的事,都被頂針默默化解了。
我也是這兩年,老想起過去的人,過去的事。有時會游蕩在她們居住過的地方,對于過去,我時常混沌,也并不總是懷念。
假如過去的事就這么過去了,未來也無非是現在的重復。
(酷玩)

【橙美文】姥姥
安徽商報
張雪子
2025-07-14 09:55:17
姥姥去世之后,我媽經常獨自坐在公交車上哭。她說:也不知怎么了,眼淚止不住。就覺得委屈,不是為自己,是替姥姥委屈。
姥姥去世的前三年,住我家。那時候,家里蹲著兩個老太太。一個奶奶,一個姥姥。她們都是多子女的家庭,在老伴接連去世之后,選擇在最小的兒女家里生活。
家是平房,很小。一處小院,一個屋子,一張炕,最里面是做飯取暖的爐子。
華北平原上的平房,蓋得密密麻麻,遠看像是無數包火柴盒扔在了地上,胡同的一側是各家各戶的門,對面是狹小四方的后窗,像小時候寫字用的田字格。有一次,三姑在我們家煮玉米。夏夜里,她光膀子就跑去后廚取玉米,看見后窗上赫然有一張臉,三姑一手拎一個玉米,“嗷”一嗓子,嚇得偷窺者末路狂奔。
上世紀九十年代有段時間治安環境不佳,社會上流行著各種各樣的事。有一陣,有人會把抄寫的冊子掖到門縫里,上面赫然寫著,抄寫二十份傳遞給其他家,可保平安……于是,家里大人小孩開始抄寫,半夜偷偷出去傳遞。當時的人們,因為消息閉塞,總被某種神秘主義所裹挾。
我家平房雖小,但人數眾多。就像那種電影里的意大利家族,日常都會圍繞在老人身邊。腳前繞,身邊繞,嘰嘰喳喳的,像老母雞身邊的一群小雞。有時候,我感覺奶奶像個漢子,姥姥像個小女人,她們是兩口子,在一起搭伙過日子。
寒冬大雪。早上我去上學,看見火爐上茶壺正沸騰,旁邊是幾個花卷,烤得微微焦黃,發出“滋滋”的聲音。一邊,炕上擺上四方矮炕桌。奶奶從缸里撈出咸菜,那是用壓菜石頭壓了整整一個秋天的芥菜,切成絲后脆軟酸香。姥姥負責泡茶,一個四方的茶葉罐,罐中是湖北產的磚茶,渡千山過萬水來到了我家。會放幾個冰果在罐子中,增加香氣。
她們兩人盤腿坐在炕桌前,開始泡茶吃早飯。我背著書包,去上學。走出門后往里看了一眼,炕上熱氣彌漫,窗欞上映照著她們的笑聲。當時我想:啥時候我能過上這種日子。
下午,她們會叫上鄰居老太太,在家里打一毛、兩毛錢的麻將。她們在老頭都走掉之后,宛如姐妹,度過了一段悠閑愜意的時光。
事情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變化的?我也說不清。據我媽的回憶,姥姥是接到了兒子的通知,讓去看孫子。兒子的老婆為人跋扈,潑辣無比。給我舅舅下了死命令:叫你媽過來看孫子!
我姥姥背著一身行囊去了兒子家。在那里發生了什么事,我都不知道。直到有一天,姥姥身體不適去看醫生,是肺癌晚期。很快,三個月左右,她就走了。
離開的時候,姥姥腦子已經糊涂,半昏迷狀態。子女們商量后,決定每個人下班去陪床。偏偏在我爸媽陪床的那天,她走了。兩人站在院子中央一臉茫然,我媽去隔壁找她的舅舅。我爸一個人在屋里不敢待,躲在院子中央抽煙。
老舅舅是過來人,一進門就說,愣著干嘛,趕緊穿衣服。幾個人開始著急忙慌地穿戴,老舅舅摘取姥姥的耳環、戒指。摘到戒指時,死活摘不下來,抹了油也摘不下來。老舅舅跟我媽說:你媽一直小心眼,這是怕我拿走呢。你來摘。我媽一摘就摘下來了。
這些事,我沒有親見,都是我媽復述的。起初只當故事聽,后來只剩唏噓。
我媽說:打發你姥姥時,請了所有親戚。沒想到當天,大舅媽和二舅媽打起來了,為了爭家產。可是你姥姥根本就沒留下什么家產,她內心更覺悲傷,戒指也沒留,給了我大姨。
前期忙忙亂亂,來不及傷心。在姥姥走后幾年,她突然悲上心頭。那時我們也搬了家,住的很遠,她每天要坐一小時公交,就利用這一小時在公交車上偷偷哭。
時間又過了很多年。早年跋扈的大舅媽最后信了佛。有一次懺悔:我年輕時候太混蛋了,開過熟食鋪子,攤過煎餅,一心為賺錢,我對不起我男人……哦,還有我的婆婆……
在我從小到大的日子,看見過很多這樣的女性。像祥林嫂一樣生活,悲苦交集,逆來順受,度過自己的一生。存在過,也沒存在過。從未為自己活,日后也很少人會想起她們。她們就像大地上的野草,簇擁映照著一兩朵野花。
當時,我覺得事情就該這樣,大地假如沒有野草,那一兩朵鮮花未免也太突兀了。直到某天我看見大黑河沿岸的薰衣草園,才發現如今鮮花也可以簇擁著生活。
姥姥臨走前,一個人在炕上縫一件衣服,她說,女人么,就像這手上的頂針。家里再多的事,都被頂針默默化解了。
我也是這兩年,老想起過去的人,過去的事。有時會游蕩在她們居住過的地方,對于過去,我時常混沌,也并不總是懷念。
假如過去的事就這么過去了,未來也無非是現在的重復。
(酷玩)
姥姥去世之后,我媽經常獨自坐在公交車上哭。她說:也不知怎么了,眼淚止不住。就覺得委屈,不是為自己,是替姥姥委屈。姥姥去世的前三年,住我家。那時候,家里蹲著兩個老太太。一個奶奶,一個姥姥。她們都是多子女的家庭,在老伴接連去世之后,選擇在最小的兒女家里生活。家是平房,很小。一處小院,一個屋子,一張炕,最里面是做飯取暖的爐子。華北平原上的平房,蓋得密密麻麻,遠看像是無數包火柴盒扔在了地上,胡同的一側是各家各戶的門,對面是狹小四方的后窗,像小時候寫字用的田字格。有一次,三姑在我們家煮玉米。夏夜里,她光膀子就跑去后廚取玉米,看見后窗上赫然有一張臉,三姑一手拎一個玉米,“嗷”一嗓子,嚇得偷窺者末路狂奔。上世紀九十年代有段時間治安環境不佳,社會上流行著各種各樣的事。有一陣,有人會把抄寫的冊子掖到門縫里,上面赫然寫著,抄寫二十份傳遞給其他家,可保平安……于是,家里大人小孩開始抄寫,半夜偷偷出去傳遞。當時的人們,因為消息閉塞,總被某種神秘主義所裹挾。我家平房雖小,但人數眾多。就像那種電影里的意大利家族,日常都會圍繞在老人身邊。腳前繞,身邊繞,嘰嘰喳喳的,像老母雞身邊的一群小雞。有時候,我感覺奶奶像個漢子,姥姥像個小女人,她們是兩口子,在一起搭伙過日子。寒冬大雪。早上我去上學,看見火爐上茶壺正沸騰,旁邊是幾個花卷,烤得微微焦黃,發出“滋滋”的聲音。一邊,炕上擺上四方矮炕桌。奶奶從缸里撈出咸菜,那是用壓菜石頭壓了整整一個秋天的芥菜,切成絲后脆軟酸香。姥姥負責泡茶,一個四方的茶葉罐,罐中是湖北產的磚茶,渡千山過萬水來到了我家。會放幾個冰果在罐子中,增加香氣。她們兩人盤腿坐在炕桌前,開始泡茶吃早飯。我背著書包,去上學。走出門后往里看了一眼,炕上熱氣彌漫,窗欞上映照著她們的笑聲。當時我想:啥時候我能過上這種日子。下午,她們會叫上鄰居老太太,在家里打一毛、兩毛錢的麻將。她們在老頭都走掉之后,宛如姐妹,度過了一段悠閑愜意的時光。事情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變化的?我也說不清。據我媽的回憶,姥姥是接到了兒子的通知,讓去看孫子。兒子的老婆為人跋扈,潑辣無比。給我舅舅下了死命令:叫你媽過來看孫子!我姥姥背著一身行囊去了兒子家。在那里發生了什么事,我都不知道。直到有一天,姥姥身體不適去看醫生,是肺癌晚期。很快,三個月左右,她就走了。離開的時候,姥姥腦子已經糊涂,半昏迷狀態。子女們商量后,決定每個人下班去陪床。偏偏在我爸媽陪床的那天,她走了。兩人站在院子中央一臉茫然,我媽去隔壁找她的舅舅。我爸一個人在屋里不敢待,躲在院子中央抽煙。老舅舅是過來人,一進門就說,愣著干嘛,趕緊穿衣服。幾個人開始著急忙慌地穿戴,老舅舅摘取姥姥的耳環、戒指。摘到戒指時,死活摘不下來,抹了油也摘不下來。老舅舅跟我媽說:你媽一直小心眼,這是怕我拿走呢。你來摘。我媽一摘就摘下來了。這些事,我沒有親見,都是我媽復述的。起初只當故事聽,后來只剩唏噓。我媽說:打發你姥姥時,請了所有親戚。沒想到當天,大舅媽和二舅媽打起來了,為了爭家產。可是你姥姥根本就沒留下什么家產,她內心更覺悲傷,戒指也沒留,給了我大姨。前期忙忙亂亂,來不及傷心。在姥姥走后幾年,她突然悲上心頭。那時我們也搬了家,住的很遠,她每天要坐一小時公交,就利用這一小時在公交車上偷偷哭。時間又過了很多年。早年跋扈的大舅媽最后信了佛。有一次懺悔:我年輕時候太混蛋了,開過熟食鋪子,攤過煎餅,一心為賺錢,我對不起我男人……哦,還有我的婆婆……在我從小到大的日子,看見過很多這樣的女性。像祥林嫂一樣生活,悲苦交集,逆來順受,度過自己的一生。存在過,也沒存在過。從未為自己活,日后也很少人會想起她們。她們就像大地上的野草,簇擁映照著一兩朵野花。當時,我覺得事情就該這樣,大地假如沒有野草,那一兩朵鮮花未免也太突兀了。直到某天我看見大黑河沿岸的薰衣草園,才發現如今鮮花也可以簇擁著生活。姥姥臨走前,一個人在炕上縫一件衣服,她說,女人么,就像這手上的頂針。家里再多的事,都被頂針默默化解了。我也是這兩年,老想起過去的人,過去的事。有時會游蕩在她們居住過的地方,對于過去,我時常混沌,也并不總是懷念。假如過去的事就這么過去了,未來也無非是現在的重復。(酷玩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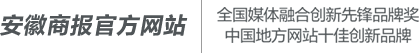
 設為首頁
設為首頁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系我們
聯系我們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