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親成為讀者時
□鄧安慶
經過后門口時,父親坐在那里看書。陽光遠遠地落在菜園的藤架上,風徐徐吹來。我問父親看什么書,父親羞赧地笑笑:“不是你寫的書?”我瞥了一眼書封,是我從北京帶回的《荒野偵探》,波拉尼奧寫的,“我的書還在寫呢。”父親摩挲書封半晌,才站起來遞給我,“那我不看了,我只看你寫的。”正好也路過的母親,見此在一旁笑道:“你認得幾個字?給你看你也看不懂。”父親瞪大眼睛回:“我兒寫的,我就看得懂!”
父親認得一些字,不過讓他看完一篇文章,還是非常吃力的,但他很好奇我究竟寫了一些什么。有時候我在二樓的房間里敲字,他會悄悄地走進來,笑瞇瞇地湊近:“寫得順利么?”我說:“順利。”一邊回他,一邊繼續打字。他默默地站在我旁邊,連呼吸都不敢加重,生怕打擾我。可是他站在那里,我多少還是會別扭,便抬眼看他一眼,他立馬感應到了,“你慢慢寫。”說著,他轉身,一搓一搓地往門口走。此時我又有些內疚,叫了一聲他,他回頭揮揮手:“你寫你的。飯熟了,我叫你。”
他總愛叫我“兒哎”。我坐在他房間看電視,他指著電視柜旁邊的礦泉水,像是獻上寶貝似的,“兒哎,你喝!那水比自來水好喝。”家里天熱,他把風扇扭過來對著我吹,“兒哎,屋里是不是好熱?”他開車去鎮上買來了排骨、牛肉、筍子等一堆菜,“兒哎,排骨燉湯,幾好喝哩。”他目光總忍不住放在我身上,而我總忍不住躲開。我怕我承受不住那目光。
他看我時,眼睛里總有歡喜。一歡喜,他總忍不住跟別人說。我總囑咐父親不要太過張揚。比如說,不要拿著我的書特意跟別人說這是他兒子寫的,他也不要說兒子在哪里做過講座發表過文章,一切都要低調。父親委屈地說:“我哪里說了嘛。”我笑笑,沒有繼續說他。其實現在我去村里超市買東西,老板娘說:“哎喲,作家回了啊!”路過菜園,垸里的伯伯從地里站起來,“文學家回了,你爸還念你嘞!”每回碰到這種情況,我都有些發窘,也知道肯定是父親跟他們老提起我。還有打牌時,他總忍不住說:“我兒寫書寫我寫得幾多。”有人笑:“是寫你愛打牌吧!”他臉紅紅:“你瞎扯!寫我好事兒。”
說來慚愧,我的確寫過父親愛打牌,寫過父親很多糗事,還寫過他脆弱的、狼狽的、傷心的、困窘的種種。我總忍不住寫他。他從我小時候高高大大的,到現在變得矮矮縮縮的;從原來的健步如飛,到現在走路要小心地一探一探;從跟人說話神采飛揚,到現在人家說十句他才反應過來一句……他老了,而我的文字記錄下了他慢慢老去的過程。
我現在回家的次數比過去那些年多了很多,每逢放假我盡量都會趕回來。父親,還有母親,已經往老年邁進了。那些肉眼可見的衰老跡象,在我看來,總是觸目驚心的。回到家,就坐在那里,陪著他們吹吹風說說話,一天悠長,日光漸漸地熄滅,星星一顆一顆地在深藍的天幕上亮起。我沒有讀書,沒有寫作,什么也不做,就陪在他們旁邊。這樣的日子,不會很多了,所以我很珍惜。
吃晚飯時,父親問我:“新書明年能出來么?”我說:“應該可以。”他又問:“到時候會做活動么?”我說:“要看出版社安排。”父親點點頭:“你要好好寫,要對得起讀你書的人。”我說曉得。父親說:“你要珍惜大家對你的喜歡。”我又說曉得。父親最后囑咐了一句:“莫寫我壞話!”我噗嗤一聲笑了,父親也笑:“兒哎,我是你爸!你要曉得。”
一生苦樂所在
□米麗宏
俗話說,地里的草、家里的貓,都有九條命,耐死。草,好像永遠鋤不盡,因此夏日鋤禾,好像是永恒的一項活計。
鋤草,最宜響晴天。陽光越狂暴,鋤禾人身上越是熬煎,心里頭越是高興。盼的就是這有勁道的陽光,它會幫人收拾這煩人的野草。
父親是個優秀的鋤者,出色的莊稼把式。生產隊時,割麥收秋,薅苗鋤禾,他是“打頭兒”的角色。每每地頭一站,鐮刀鋤頭一上手,他的身份地位剎那提升。他成了元帥,他要身先士卒,做出表率。他的位置永遠在最顯眼的地方:人們正中間的那一壟,那一壟的第一個。那么多雙眼睛注視下,他悠悠喊一聲“開鐮嘍——”或者“間苗兒嘍——”之后,割下第一鐮,耪下第一鋤。這是起點,也是360度無死角審視下的完美開始,是禁得起打量、挑剔的標本。以他為首,兩翼緊隨,一個箭形梯隊,緩緩行進在黃綠色田地里。
那是父親作為一個農民最輝煌、最快樂的記憶了。
父親做“打頭兒”,一直到生產隊解散。后來,跟在父親身后的,只有我們一家人了。有時,我一邊近乎癱軟地拉著鋤頭,一邊偷眼看他:他的動作有板有眼,抑揚頓挫,不知疲倦,身體里仿佛裝著一臺永動機。豫劇《朝陽溝》里唱:“那個前腿弓,那個后腿蹬,心不慌來手也不要猛”……他就有那種沉靜入戲的狀態。他輕輕把鋤頭送出去,鋤尖兒落地,銀亮的鋒口吃進土里;他順勢一拉,騰起一陣輕微塵煙,雜毛亂草紛紛撲地。鋤頭過處,像被剃過的頭,土層松軟,一棵棵苗兒裊裊而立。
他雙腳一前一后,踩在鋤過的壟里,浮土松軟得沒住鞋幫。父親向我做示范:鋤頭吃土最少一寸厚,這樣,草也死了,墑也保了。
對于我,鋤禾是一種高強度體力消耗,重復機械的動作,枯燥得難以忍受。鋤不了幾壟,腰酸,胳膊疼,手掌起了泡。烈日越來越暴躁,人幾乎處于半灼傷狀態,汗流滾滾,越過眉毛,直抵眼球,辣得睜不開眼。一時,渴來了,餓也來了,又累,又曬,又暈……我在地中央埋怨,甚至撂下鋤頭踅入地頭的蔭涼。父親開始講故事。我現在感覺,他與其說是以故事來賄賂我們干活兒,還不如說是為調節鋤禾的氣氛。每講故事,他有個開場白:“說故事,道故事,北邊來個傻小子。撿了十八個蛋,孵了十九只雞……”我一聽,用衣襟“胡嚕”一下臉上的汗,磨磨蹭蹭過來了。
父親講三俠五義,也講南征北戰,還講村里人去北河叉王八……有一次,他講1971年去沙河建朱莊水庫,搞夜戰,一直干到凌晨兩點,挑擔運沙,大腦已酣酣入睡,兩腿還在前行,好像是靠著腳趾自動找路面。踩到水溝里時,一聲大叫,徹底醒來……那時,為了跟上父親的速度,我不敢放松,因為一放松就會漏掉故事情節。
臨近正午,太陽愈加猛烈。父親讓我們去樹蔭下歇涼,由他來完成最后幾壟。我在蔭涼里看著他,他那被陽光照得明亮而萎靡的臉,彎成一張弓的腰,褲腳處滴滴答答的汗水,那背上凝出的一圈圈白漬鹽粉。我暗暗發誓,有朝一日,一定讓父親脫離這種煎熬的生活。
多少年后,我曾幾次試圖將他從土地上遷走,讓他跟我在縣城里過那種悠閑自得的老年生活;可是,每次都失敗了。他像一棵被無情拔離土地的莊稼,萎靡失落,時不時嘆息,說自己活著沒了樂兒。“地頭吸支煙,炕頭喝盅酒,鋤地回來歇個晌”,那樣的日子,才是最大的享受。
終于明白,對于父親而言,鋤禾耕稼,不是熬煎,不是苦楚,而是事業,是一生苦樂所在,是天正地正的本分,是他在這個世上生存的意義。
父愛沒有保鮮期
□聶難
父親離開兩年了。每當推開老屋吱呀作響的木門,墻角那把銹跡斑斑的鋤頭、窗臺上蒙塵的搪瓷杯,都還殘留著他的氣息。時光帶走了他的體溫,卻沖不淡記憶里那些浸潤著父愛的瞬間,原來父愛從來沒有保鮮期,它像深埋地下的老酒,愈久彌香。
兒時的夏天總帶著蟬鳴的燥熱。我在曬谷場瘋跑時摔破膝蓋,鮮血混著泥土糊了半條腿。正在田里勞作的父親聞訊趕來,草帽歪斜地扣在頭上,褲腿還沾著泥漿。他粗糙的手掌小心翼翼地托著我的傷處,往家走的路上,將我穩穩背在背上,自己的后背被日頭曬得通紅。回到家,他用井水沾濕毛巾,一下又一下地擦拭傷口,每擦一下都輕輕吹氣,仿佛這樣就能帶走我的疼痛。那時我以為,父親的關懷就像屋檐下的陰涼,只要待在他身邊,就能躲開所有風雨。
上高中時,我要到70多公里外的縣城讀書。開學那天清晨,父親扛著裝滿被褥的蛇皮袋,走在前面為我開路。從村里到鎮上的路坑坑洼洼,他走走停停,不時回頭確認我的腳步。到了鎮上搭班車,他把皺巴巴的學費塞進我手心,反復叮囑:“想吃啥就買,別餓著。”車發動時,我透過車窗看見他站在原地,身影越來越小,卻固執地揮著手,直到消失在我的視線里。
每個月回家,父親總會提前算好時間。若是趕上周日返校,凌晨四點,廚房里就會亮起昏黃的燈光。我揉著惺忪睡眼,看見他蹲在灶臺前生火,火苗映照著他布滿皺紋的臉。鍋里咕嘟咕嘟煮著臘肉面,那是我最愛吃的。他把熱騰騰的面端到我面前,自己卻只啃著冷硬的饅頭,說:“我不愛吃這些,你多吃點。”可我知道,那是他把最好的都留給了我。
高考前那段日子,我壓力大到整夜失眠。父親察覺到我的異樣,雖不識字,無法像其他家長那樣寫鼓勵的話語,卻用最質樸的行動支持我。每天天不亮就出門,步行兩個多小時,到鎮上買回我最愛吃的豆腐腦。等我起床時,碗里的豆腐腦還冒著熱氣。他坐在一旁,粗糙的手指局促地摩挲著衣角,欲言又止,最后只是輕聲說:“盡力就好。”有次我半夜醒來,看見他坐在堂屋門檻上,借著月光編竹筐,說要給我裝書本用。竹篾劃破了他的手,他卻渾然不覺,只想著能為我多做些什么。
兩年前的國慶假期,城里處處張燈結彩,而我卻接到噩耗。匆匆趕回家時,老屋門口的玉米還掛在稈上,金黃的穗子在風中搖晃。父親躺在堂屋竹榻上,形容枯槁,床邊放著我給他買的新外套,一次都沒穿過。我握住他冰冷的手,怎么也不敢相信,那個曾為我遮風擋雨的人,就這樣離開了。
如今,每當走過父親生前常去的老井臺,看見鄉親們在那里洗衣聊天,我總會駐足良久,仿佛還能看見父親挑著水桶,沖我咧嘴微笑。清明掃墓時,我帶著父親愛吃的紅燒肉,擺在他的墳前。山風掠過墳頭青草,恍惚間,又聽見他在耳邊說:“別太累,照顧好自己。”
父愛沒有保鮮期,即使父親已不在人世,他的愛依然滲透在生活的每個角落。它是凌晨灶臺上的一碗熱面,是步行兩小時帶回的豆腐腦,是粗糙手掌編織的竹筐。這份愛早已融入我的血脈,成為我面對生活的底氣。我知道,無論時光如何流轉,父親的愛都不會消逝,它將永遠陪伴著我,在歲月的長河中,溫暖而堅定地閃耀。
“阿姨”成了“老頭子”
□陳衛華
前幾天,接到我爸一個電話。電話接通后,我爸的開場白就是:“三子,我跟你說一件事情。”這幾年來有好幾次,這個開場白的后面接著的都是他遇到難題時向我的求助。他自己不一定意識得到,但我已經習慣了。我猜想,他這個開場,也許是因為作為父親竟然要向兒子求助,覺得有點不好意思,所以才特意將求助打扮成了告知?當然,也有可能是我多想了。
這次他打電話來是因為,他想在手機上下載一個萬年歷,查看節氣之類的一些信息,結果在操作過程中,需要填手機號。他填了手機號后,有人打電話給他要驗證碼。聽到這里,我內心已斷定他遇到了詐騙,但想到他一個農村老頭,能被騙的錢也不多,我也沒緊張。結果情況比我想象的要好,他說,給了驗證碼后,他收到一個短信,說他訂閱了某個服務,每個月要扣30塊錢話費。
對于我爸這樣,夏夜不熱得受不了都不舍得開空調的人,一個月扣30塊錢,那是天大的事。他急得不得了,先是跑到鄰村去找到我的小姑父、一個比他年輕幾歲的農村老頭。小姑父也沒遇到過這種情況,把他帶到了牌友們正在酣戰的牌場,尋求群眾智慧,還是沒人提出解決方案。兩人決定,第二天由小姑父陪我爸一起,到縣城的中國移動營業廳去取消該項訂閱。
可能是心里還是沒有底,他才打了我電話。我告訴他,不要著急,先打110報警,把整個過程敘述一遍,警方見識過的各種詐騙類型太多了,他們的指導肯定更加專業。
過了20分鐘,我又接到電話,我爸說,他報警后,警察讓他打10086,他打了之后,對方直接幫他取消了訂閱,他已收到短信了。我叮囑他,以后凡是驗證碼,一定不能告訴別人,他感慨:以后再也不敢下這些東西了。
當時我正跟一個同學在一起,同學好奇問我:你爸多大了,還會用智能手機?我說虛歲80了。他說他爸80多了,在家一直用的都是老年機。
確實,我也佩服過我爸。一次回老家,看他在手機上看新聞,想到他無人教就能掌握智能手機的基本使用,覺得還挺厲害的。我贊嘆了幾句,我媽在旁邊補充說,村里有紅白喜事喝酒,擰開的酒瓶蓋可以掃碼領紅包,年輕點的都是把瓶蓋給我爸掃。年輕點的會掃,但需要尊老。被尊老的群體中,也就只有我爸會掃碼領紅包。
我爸能用老年手機,離不開他的終身學習理念。當然,他是自發的。他是小學畢業的水平,在同輩人中算是文化人,當上了村里會計,直到后來生產隊解散。
農閑時,他喜歡看書,能找到什么就看什么。有時候,還拿我們的練習本或幾張空白的紙,編一些順口溜。前幾年,我回家,他還送了一張紙給我,上面是他總結的一些做人道理,其中一句是“心口常守防出錯,假癡不癲是智人”。還有一次回家,他送我一張紙,上面是他工整抄錄的五臟六腑養生口訣。每次我都是鄭重地接過來,但一回城,那張紙就不知被我放哪兒去了。好在我拍了照片,估計在我的百度網盤里都能找到。
我們村的家譜已經流失,前幾年他又憑著記憶以及詢問同齡人,制出一份簡易家譜,雖然從他那輩算起,只上溯了三四代,但也引得不少人來我家參觀,追根溯源。
小時有一件事一直困擾我,就是對父親的稱呼。我們那邊對父親的稱呼有好幾種,我家里是喊阿姨(音)。小學時,我已知道,阿姨是指跟媽媽同輩的其他女性,心里嘀咕,我怎么能喊父親“阿姨”呢?再后來學了木蘭詩,詩中有“阿爺無大兒,木蘭無長兄”,我猜阿姨應是阿爺的方言轉音。
我同村的孩子中,有的喊父親dada(第一個字陰平聲,第二個字陽平聲),估計是大大的轉音。有的喊父親老姨,應該是老爺的轉音,因為他父親在兄弟輩中最小。當然也有喊爸爸的,但我懷疑可能是伯伯的轉音,因為他父親在兄弟輩中是老大。
我的手機里,我爸的微信號我備注為“老頭子”。漢語中常常一詞多義,老頭子在我們那邊,既可指老年男性,也可指父親,用起來貼近又親切。當然,當面對話的時候,我還是規規矩矩叫一聲“阿姨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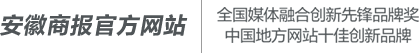
 設為首頁
設為首頁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系我們
聯系我們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