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市的生活如被擰緊了發(fā)條,人們總像是在齒輪與齒輪之間旋轉(zhuǎn);耳中常有的是手機(jī)的提示音、地鐵進(jìn)站的呼嘯聲和路上行人的腳步聲,重重疊疊的聲響如同無(wú)形的枷鎖,將我束縛在這日復(fù)一日的循環(huán)里:時(shí)間被精密地測(cè)算,生活里每一分每一秒似乎都有它固定的歸宿。

我抬頭看著白色的天花板,有些迷茫,去哪才算自由?不被城市所束縛?微微側(cè)目,我看向墻上的中國(guó)地圖,視線不斷的聚焦、聚焦……
呼倫貝爾?對(duì),呼倫貝爾!
抵達(dá)草原那刻,帶著絲絲泥土氣息的風(fēng)便撲面而來(lái)。城市里被高樓擠壓得不成形狀的風(fēng),在這里也終于尋回了天然本貌——它無(wú)形卻無(wú)處不在,卷起草葉,攪動(dòng)湖面,在耳畔呼嘯出北方草原的歌謠。極目遠(yuǎn)眺,視線再無(wú)阻礙,仿佛是大自然刻意撫平的一片土地。不遠(yuǎn)處有個(gè)穿著白裙子的小女孩正迎著陽(yáng)光向前奔跑,光的所到之地仿佛和風(fēng)有著約定,一同透過(guò)她的發(fā)絲,散發(fā)著自由的暖意;低頭俯看這綠油油的草坪,我不禁躺下身去,草甸的柔軟仿佛大地伸出的手掌輕輕托住了我,泥土與青草氣息蒸騰而上,沁入肺腑,仿佛在滌蕩沉積已久的塵埃。蒼穹之上,莫日格勒河上空的云也是那樣的自由,不像漫畫書里的規(guī)整棉花糖,也不像數(shù)學(xué)公式那樣排列整齊,它們無(wú)拘無(wú)束,它們可以是一大片的層積云,也可以是隨意安置的小小積云,它們無(wú)須奔赴何方,亦不必追趕分秒,時(shí)間似乎也甘愿在這里駐足,流連于這片小小的世界。

次日,我們便到了黑山頭馬場(chǎng),聽聞那草原之魂,就在駿馬奔騰的壯觀中,在朱霞爛漫的壯美里。剛上馬時(shí),我還有些束縛,腦海中還在閃現(xiàn)網(wǎng)上馬兒受驚的場(chǎng)景,但當(dāng)前方領(lǐng)馬的牧民一聲呼哨,甩起他的長(zhǎng)鞭時(shí),馬兒們便整整齊齊地一路小跑在草地上,風(fēng)在耳畔的呼嘯聲愈來(lái)愈大,大地被馬蹄叩擊,聲聲如密集的鼓點(diǎn),顛簸之間,只覺(jué)得久被電子設(shè)備禁錮的四肢突然間掙脫了無(wú)形鎖鏈,感覺(jué)骨骼都完全伸展開來(lái),飛馳的自由感竟讓那一刻的我完全忘卻了學(xué)校社團(tuán)安排的重重任務(wù)、忘卻了生活上不如意的種種瞬間、忘卻了在空閑時(shí)光里無(wú)所事事的盲目感……
夕陽(yáng)西沉,我們爬上山頭,晚霞如赤紅的火焰在天際綻放。蜿蜒的河流緩慢的延伸著,延伸至那廣闊的天邊,火紅的太陽(yáng)被巨大的云層吞噬,云層下方是早已染上金邊的日暮,云層上方卻還有白日里淡淡的藍(lán),游客們紛紛舉起相機(jī),將這曠世的美景默默珍藏。腳下是堅(jiān)實(shí)的大地,頭頂是燦爛的長(zhǎng)空,霞光映紅了每張真誠(chéng)的笑臉,遠(yuǎn)處還有牧民的歌聲裹挾著粗獷的喜悅,直沖云霄,仿佛是那遠(yuǎn)古的回聲。

直到萬(wàn)物都染成深琥珀色,熔金里的那輪太陽(yáng)才肯一點(diǎn)點(diǎn)靠近地平線。遠(yuǎn)處蒙古包的炊煙還在與晚霞糾纏,想牽住最后一縷天光,而腳下的草浪早已被染成深淺不一的紅。我忽然懂得為何人們說(shuō)“日落是草原的心跳”,因?yàn)檫@一刻,無(wú)需多言,風(fēng)聲里全是答案。
原來(lái)人終需奔向這樣的曠野,才能尋回自身那被喧囂吞沒(méi)的身影。它藏在馬背上顛簸的快樂(lè)里,藏在看往落日余暉的目光里,藏在夜色籠罩時(shí),對(duì)著那干凈透亮的夜空中浩瀚星河的感嘆里。
呼倫貝爾的風(fēng),掠過(guò)草原,跟著那歸程的車掠過(guò)柏油路,來(lái)到城市,然而曾經(jīng)的喧囂在我心中已然不同:我的呼倫貝爾,那遼闊無(wú)垠的草地,那奔騰不息的生命力,已悄然沉淀于我的心底,成為對(duì)抗浮躁的定海神針。我們不能一直呆在草原,逃避現(xiàn)實(shí),而去往草原的旅途卻給予我自己內(nèi)心一方凈土,讓我的呼吸里,也常存著青草與泥土的芬芳。自由,原來(lái)也并非只存在于草原,只要心中有這樣一片草原,在擁擠的塵囂中也能有內(nèi)心的遼闊。
再見,我的呼倫貝爾!
再見,我的草原!
(文圖:安徽農(nóng)業(yè)大學(xué) 張思辰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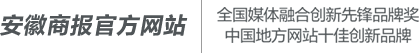
 設(shè)為首頁(yè)
設(shè)為首頁(yè)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(lián)系我們
聯(lián)系我們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