油菜花將村莊舉向高處,灼熱的陽光從天空澆灌下來,萬物都在發光。
父親告訴我,家里的那對燕子一周前回來了,上午十點進門,在堂前飛了兩圈又飛走,之后就不見了,不知道去了哪里。
母親一個勁嘀咕,怪父親不該在屋梁掛許多雜物,燕子嫌這屋子亂糟糟,換了別人家重新筑巢了。父親說不會的,燕子戀舊巢,肯定會回來。果然,第三天上午,那對燕子又回到屋里,嘴里銜著新泥,開始一年一度修補舊巢的工作。
自從這對燕子幾年前在我家落戶,春分后能否如期返回,就成了父母最惦記的事,當它們重新出現,像兩道弧光飛進飛出,將活潑潑的生命氣息帶進屋子,我們家的春天才算真正到來。
春分后的每個早晨,我都帶著相機去往浦溪河的楓楊林,在林子里來回地走,與林中的老鄰居重逢,與新鄰居相見,聆聽鄰居里的歌唱家在這個時節展示的音樂才華,觀看隨時上演的林中春天故事。
近兩日林子里最活躍的鳥當數松鴉,還沒進林子就聽見它獨特的煙熏嗓發出的單音節:“啊、啊、啊!”很快,兩三只松鴉從林子里飛出來,接著又飛出兩三只,再飛出兩三只,一路追逐向著林子的另一邊飛去,邊飛邊叫,撲打鬧騰,一對對在樹頂落下足后,才安靜下來。
松鴉不止一種嗓音,除了煙熏嗓,它還會發出類似美聲唱法的嗓音,高亢,圓潤,叫一聲,停頓片刻,再叫一聲,音調頗高,帶著幽怨之意,聽上去像是失戀者的悲嘆,當然這只是我作為人的感受,在松鴉的語言里,這樣的鳴聲很可能是高調的求偶歌,或者是向林中居民宣布領地的口號。
這林子里的居民除了鳥類、昆蟲,最多的就是松鼠了。
如果說那只孤獨的領鵂鹠是這片林子的首領,那么松鼠就是林子里的大王。首領只有一個,大王卻有很多,多到沒有辦法知道它們的數目。松鼠可不像領鵂鹠,只在林子中間最高的樹上蹲著,很少挪動地方,仿佛它的寶座就是那棵樹。松鼠是不需要固定寶座的,每一棵樹、每一片草地都是它們的移動寶座。松鼠太不安分了,太自由了,從樹下竄到樹上,從一棵樹到另一棵樹,隨心所欲,縱橫跳躍,一副“本王在此,看誰敢惹”的樣子。
也不是什么鳥都不敢惹松鼠,今早就看到一對松鴉,差點兒跟松鼠打斗起來。起因是這樣的,這對松鴉正在樹頂卿卿我我,忽然就沖上來一只松鼠,將兩只松鴉分開,橫在中間。
松鴉亮起它們的煙熏嗓啊啊大叫,飛起來,又落下,落在松鼠身邊,其中一只可能是雄鳥,頭上的羽冠豎起,大啄了松鼠一口,眼看著一場“二松之戰”一觸即發。可松鼠這混不吝的家伙,毫無戰心,對自己的冒失行為也不在乎,抱著枝頭剩下的干果,美滋滋地啃起來。
松鴉見松鼠并無挑釁之意,怒火也就消了,豎立的羽冠落下,站在一邊,等松鼠吃完果子離開。兩只松鴉一只松鼠,在那棵樹的頂端,各自為營又相安無事地呆了好一會兒,等啊等,松鼠還是不走,抱著干果只管啃。
松鴉可能覺得實在太無聊,一前一后飛走。松鴉飛走后,那只松鼠依舊抱著干果啃食很久,對松鴉的離去渾然不覺。
這些小動物們在同一片林子里住著,總有故事不停上演,而我作為人類,一天中最大的快樂就是讀到這些故事。(木舍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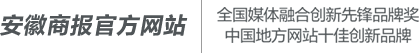
 設為首頁
設為首頁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系我們
聯系我們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