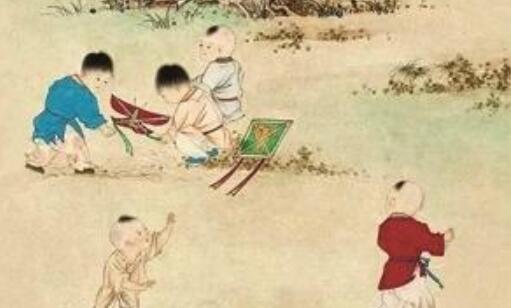豆子長在豆埂之上,這句話好像有些多余,其實不然。在家鄉,所謂豆埂,多是水稻田的田埂。水稻栽過以后,田埂上的雜草被清理干凈,莊稼人見不得有一點的土地被浪費,見縫插針在田埂上種上豆子。種上了豆子的田埂,才會被人稱作豆埂。
老家種豆,不叫種豆,叫點豆。水稻剛剛栽下田,正返青呢,家里的農活暫時不太忙了。清晨,爺爺將上衣的口袋里裝滿豆種,對正在廚房里忙著的奶奶說,我點豆子去了。奶奶從灶口探出頭來,對爺爺說,東邊溝、三畝半、小山、前沖的豆埂都要點上,還有小圩,小圩的豆埂出豆,稍微點密點,不礙事。爺爺不吭聲,哪一條豆埂上的豆子該點密一點或點稀一點,他是最清楚的了。爺爺背上一把稱手的鐵鍬,出門點豆去了。
點豆,多少有點像是技術活,沒干慣,是點不好的。可對爺爺來說,點豆是輕省的事,熟練得如同兒戲一般。爺爺右手將鐵鍬的尖在田埂上輕輕一插,左手隨手丟一兩粒豆子在鍬尖處,提鍬將鍬尖挖開的土輕輕一搗,搗碎的土覆蓋在豆子上,就點好一穴豆了。爺爺沿著稻田的田埂走過來,邊走邊點,用不了一盞茶的功夫,一塊大田的兩條豆埂上的豆就點好了。
看高瘦的爺爺點豆,是一種享受,那樣隨意輕松。我也學著爺爺點過豆,累不說,還點不好,不是將豆種丟進田里,就是將豆穴挖得深了,要么就是點得疏一棵密一棵。當然,豆子點得疏與密,不是馬上就能看得出來的。
早稻成熟,正是雙搶時節,奶奶到田邊送午茶點心,看見豆埂上的豆子,稀密高低各不同,笑著問爺爺,這豆是銅勝點的吧。爺爺呵呵地笑笑,不置可否。我試著點了幾回豆,但始終也沒有點得像爺爺一樣漂亮。爺爺點的豆,整齊的豆棵長在田埂上,既不會影響干活的人在田埂來往,豆棵也不會往稻田的方向長偏,遮了稻子的陽光。點豆,一直是爺爺的一手絕活,可惜的是,我一直也沒有學會像爺爺一樣,點出一豆埂像樣的豆子。
在村里,點豆是不能點滿一塊田的四方田埂的。一家一戶的田挨著田,你在自家田的四方田埂上都點了豆,那田塊相鄰的人家上哪兒點豆呢。點豆一般只能點兩方田埂,也就是說一塊方田的四方田埂中,只有兩方是屬于你家可以點豆的豆埂。這兩方田埂一般是約定俗成的。鄉里鄉親的,誰也不愿意輕易打破這樣的規矩。
在村里,左鄰右舍間大家都遵守著的那些微小的規矩。這些規矩,折射了鄉村生活的智慧和哲理,又有著可親可近的溫情。
豆埂上的豆子,不用施肥澆水,自然生長著,成熟了,收回來,也沒有人太在意它的收成如何。豆子青著,豆莢飽滿了,去田里干活時,順手拔了幾棵豆子帶回家。摘下豆莢,剝了豆子,毛豆清蒸,或放點辣椒蒜末姜絲清炒,或是加兩個雞蛋燒湯,味道極鮮。
我最喜歡的還是炒鹽豆子。豆子曬干,炒至半熟,撒一點雪花鹽,即可。冬日夜讀,泡一杯清茶,備一小碟鹽炒豆子,讀到開心處,順手抓數粒鹽豆丟進嘴里,滿嘴生香,真是人生一大快事。(章銅勝)


 設為首頁
設為首頁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系我們
聯系我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