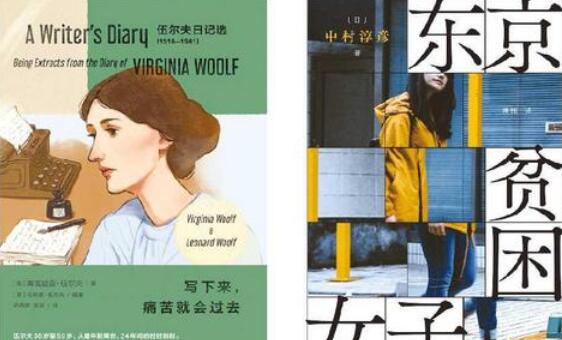小城有個搞篆刻的人,曾在湖邊小飯店里燒一手好菜,最出名的有一味“氽烏魚片”。大盤,呈上烏魚片,嫩而香,端上桌,烏魚片上的白芝麻還有滋滋響聲,令人口水欲滴。
小飯店臨湖,雖小,卻自得一湖風月。墻上還有一些書畫。對這位氽出烏魚片的篆刻人刮目相看,他贈我一枚印,款名“煙云供養”。打算按時令到湖邊嘗嘗他的另一些特色菜,主要是看湖,順便學做“氽烏魚片”。哪知一個月后,他關了飯店。他覺得世上許多事比做“氽烏魚片”事大。
他刻過一枚“生腐突爐子鍋”的印,送人。“生腐突爐子鍋”是小城特色菜,名字特點在于這是個倒裝句,本應是“爐子鍋突生腐”。“突”是動詞,方言,字形像一個倔犟的拳頭。但小城人就要跟著傳統倒著念“生腐突爐子鍋”。這菜名像小城密碼,甭管走到哪里,只要對上暗號,那就是親人,不說二話。
我見過“生腐突爐子鍋”這枚印。石質硬,他下刀果決,把生腐的“腐”字刻破了邊,似生腐在油鍋里炸出的孔。他刻的“突”字,那個拳頭格外大于其他幾個字。
桂花開時,“生腐突爐子鍋”開始上桌,但小飯店早已門庭改換。八月桂花香,小飯店門邊的那棵老桂樹如期開落。
喜歡吃一口“氽烏魚片”。我也在小城到處訪,吃來吃去,味道還是差了點。
這到處訪“氽烏魚片”,是看陸文夫文章后學的。陸文夫為了美食,特地買個竹籃。蘇州小巷哪家新飯店開業,他蹬個舊自行車,車前掛個竹籃,去買。
“好吃”能成“家”,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。
我少年在鄉下,一聽說某人“好吃”,一定是和“懶做”兩字掛鉤,這人人格立即矮化下去了,將來相親都麻煩。哪承想,偏是有那么一個因“好吃”而成了“家”的人,把一篇篇美食文字,寫成了熱氣騰騰的經典,被封為美食家。
美食家陸文夫難得寫個小說,“吃”的細節也絕不會放過,果真把“行萬里路,嘗百口鮮”,落實得一絲不茍。這美食的文字在我眼里晃蕩久了,就一直記掛著。小城不是蘇州,但小城幾家美食店還是有的,比如一家“姚記鴨湯”,一家“好再來土菜館”,一家蒙古的羊肉店,都是好吃的店。
回味吃過的每一碗菜香,本身就是詩意。
今年爸爸生病,我給他送過幾次飯。頭幾次,我認為好吃的,他都不滿意。爸爸說,煮點稀飯,白米煮。白米煮的稀飯是他熟悉的味道,他說,好吃。一個咸鴨蛋,爸爸吃得津津有味。爸爸一吃咸鴨蛋,就會說我在外地上學的事,說自己出差轉多少趟車,來到我的學校。一個公文包里塞了十來個煮熟的咸鴨蛋,我一口氣吃掉六個。爸爸說話的神情滿足又惆悵。
爸爸出院那天,我燒了一盆魚。魚塊洗凈,備好姜蒜,大火把黑陶燒熱,魚塊下鍋,第一道火候加黃酒姜蒜除腥,第二道火候加醬油著色,第三道火候加啤酒增香,適當加水,大火改小火,微燜,加小米辣、花椒油,入辣味與椒味,至魚湯漸濃,鮮味溢出,出盤時加一點熟白芝麻,提鮮,撒蔥,綴綠色。盛魚的是白瓷盤子,上面有一首辛棄疾的詩:稻花香里說豐年,聽取蛙聲一片。
燒魚時忘了燒飯,有了魚湯,沒有飯,對不起魚。轉而淘米做飯,等飯片刻,魚湯味已在誘惑,仿佛案上的幾本書,一本陳從周的《說園》,一本吳曉東的《文學的詩性之燈》,一本殘雪的《蒼老的浮云》。在廚房里看書,看幾頁,丟幾頁,沒關系,書在等人,像一碗魚湯在等飯。
(王漢英)


 設為首頁
設為首頁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系我們
聯系我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