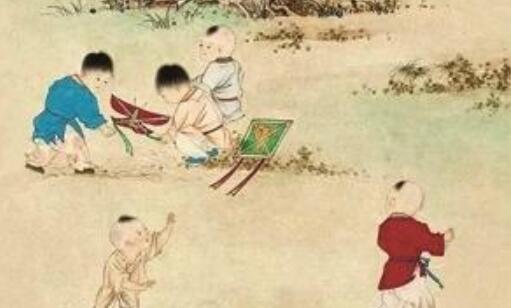郵差父親
□江星
父親是一名鄉鎮投遞員,這份工作干了16年。沒有輝煌的業績,卻也曾經做過一些“善事”,讓人欽佩。
當年,作為一名鄉村“郵差”,父親面臨投遞點多、線路長、沒有水泥路的艱難,從無一句怨言。晴天不算什么,最多與自行車一起吃點灰。要命的是下雨天,泥巴將車胎包裹得嚴嚴實實,父親只能時不時地停下來,摳掉車輪上的泥巴,一會兒車騎人,一會兒人騎車。即便如此,明知道這活兒并不輕松,他依然每天把成堆的報紙、信件沿路派送,來回幾十公里,從未停歇過,即使風霜雨雪,即使感冒發燒。
有一年夏天,暴雨傾盆,父親騎行在鄉路上,身上的雨衣早已不管用,全身上下濕漉漉。當路過一個小山坡,他停下來,將裝滿報紙和信件的郵包先卸下來。因為郵包里有著一份重要信件——高考錄取通知書。父親先將郵包送至山坡上面,再返回來扛起自行車上坡,哪知雨點實在太密,路面泥濘不堪,父親腳下一滑,一個沒站穩,連人帶車滑下山坡,好在父親的身上沒有受到很大的傷,他又扛起自行車,一步一步爬了上去。當全身濕透的父親出現在考生家里,家長驚愕地說:“我的天,這個暴雨天,師傅你是怎么騎過來的?”父親憨厚地笑笑,家長手捧通知書,掩飾不住孩子被大學錄取的喜悅,為了感謝父親,非要挽留他吃飯,并換身干凈的衣裳,父親推辭不過,只好答應。那一頓飯,可謂賓主盡歡。
晚上,父親到家清理郵包,才發現考生家人又在里面放了一袋糖果、一包煙。從此,每年高考,父親都要講述這段歷史,表情總是抑制不住郵政人的自豪和幸福。我也時常在想:正是父親每一次的盡心盡責,才受到每一個收件人的欽佩和贊譽。
記得有一年雙搶收稻,母親叮囑父親早些回來挑稻穗。父親當然曉得母親一人忙不過來,所以,那天他騎車格外快,就是爭取早一分鐘到家。但是,在快到家的路上,父親隱約聽見求救聲,隨著車輪的往前滾動,他突然看見遠處小凼里,一個雙腳陷在淤泥里的小男孩,兩只手不斷在空中亂舞,嘴里呼喊著媽媽,父親邊加速騎車,邊朝那戶人家大喊:“家里有人嗎?你家小孩掉到小凼里了,快出來啊!”說話的同時,父親急忙跳下車,向小男孩方向跑去,拼力拉住了小男孩的胳膊,將他拽了出來。小男孩媽媽聽見父親的喊聲,快速跑到了外面,見此情形后,怕得不行,對著父親千恩萬謝。父親看到小孩沒事,急忙往家里趕,到家根本就沒提這件事情。
直到第二天,那個孩子的媽媽領著兒子到家里,買了許多禮物做謝禮,我和母親才知道父親做了這件善事。那個媽媽還有個請求,一定要我家和他們家結親戚,以示感謝。父親微笑著拒絕:“你們的感激我收到了,我相信這是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應該去做的事,我不能需要任何回報,看到孩子平安無事,我很心滿意足。”
其實,在我心中,父親就像是跟隨他多年的那輛郵車一樣,不論風雨,始終穿梭在堅韌和善良的道路上。他雖是一名郵差,但他郵包里裝的不僅僅是報紙和信件,還有愛與關懷。我會記住他的每一次微笑,每一次援手,他的這種精神將影響我一生……
一直在練習告別的我爸
□徐燕
回家前,先和我爸視頻一下,問他要買什么,他好象認真地考慮了一下,說,藕粉。上次買的吃完了,覺得蠻好的。我在網上下了單,估計到家正好可以取貨。我的爸爸,現在已成了一個如同孩子的老人,取悅他不需要太多。視頻里的他蒼老得令人心碎,老而不衰,我很欣慰,畢竟,今年的他八十一歲了。
很早以前就覺得我爸老了。在他送我上大學的那天,看他扛著一個木箱子,跟在他身后的我居然心頭一酸,眼里蓄滿淚水。那會感覺到,我不小了,他還要為我承擔這么重的負擔。現在想來,真是矯情。我上大學時不到20歲,我爸那會兒最多也就五十歲呀,不過是和今天的我年紀一樣。
只能說,出門上學,我血脈里關于親情的一章突然覺醒了,看到了我爸的存在。
前陣熱播的《我的阿勒泰》,里面打動我的唯有那一句,喜歡你,是我看見你了。同理可證,以往一切,我爸的存在都是理所當然而不顯影的,但是,從到合肥那一天起,我感知到了他的存在,他提醒著我,我長大了,他變老了。
有機會從家鄉到合肥來工作,一開始我爸是同意的,并幫我向原來的單位領導打招呼,為我善后。但是,半年后的我失業了,回家過年時,又是他不同意我再出去,怕我吃苦,更怕我耽誤個人生活。那頓飯,我一句話說不出來,只會流淚,但過了年,我扛著一床被子出門時,我爸什么也沒說。
工作后不再向家里要錢,成了一個自我要求,但,當方正公司的一個朋友與我說起公司處理庫存電腦,我向我爸提出借錢。我回去時,他已經給我準備了一個信封。
那一年,工作略有起色,電話里向他表示,想在合肥買套房,他立刻答應,并說,家里能給你三萬。那會我的存款兩萬多,正好夠第一套房的首付。那時的我尚未結婚,那套房到今天,不僅增值近十倍,更成了日后我做所有選擇的底氣。
在合肥漂泊幾年,終于進了一個大公司。公司要求住宿舍,之前在合肥累積的各類家什成了累贅,我爸帶了一輛車前來幫我收拾,那些多余的東西都搞回家。多年后發現,家里的盆還是當初我拿回來的。
我不太敢嘲笑那些所謂的啃老族,從某種程度上來說,我啃的也并不少,并非金額多少,而是那種有求必應的支持。讓我在異地,即使常常遇到低谷,也不灰心不后悔,碰的南墻再硬,也不至于絕望。
后來,我爸真的老了,我們不自覺地早已換了位置。怕他退休后寂寞,我給他買ipad,買電腦,教他學會分享我的視頻平臺賬號,盡力滿足他的需求,他打我電話時,我總是耐心的,但愿他永不失望。
去年陪我爸住院的時候,我一邊絞個熱毛巾給剛做過霧化的他,一邊開玩笑問他,感覺沒白生我吧,他微微點頭。我們都笑起來,這是最幸福的時刻吧,我想。
以前,一想到父母有一天不在,立刻熱淚如傾,無法繼續,但現在,我好象可以面對了,并且為必將到來的離開做著心理準備。我爸在七十多歲時,就開始說,活不了幾年,他頭腦清晰地開始安排一切,他給家里電線重新走了一遍,換了電視、冰箱、熱水器,他是考慮他走了,我媽還要好好活著。
他銀行存單到期的,就交給我,存到我的卡上。從去年開始,他已經不存定期了,年末我回家的時候,就直接讓我去取出來,他也讓我媽將她的銀行卡用我的生日做密碼,讓我媽要記得他的東西收在哪里。
一直在練習告別,不僅是真正那天到來時不要驚慌,也是讓我們更珍惜當下在一起的日子。他總是說,人總是要死的,都不死,地球都站不下,但我心里總有個倔強的聲音,地球那么大,總不會少一點我爸生活的空間吧。
我就是希望,我的爸爸能活得久點,再久點,因為他那么那么的好。
父親的光芒
□許冬林
童年的三月,是鋪滿了粉白粉白陽光的,陽光下的那些舊事,像掌心里新搓出來的湯圓,沾著白撲撲的粉,有著人間的吉祥與俗氣。在這樣的三月里,父親像主角重回舞臺,他脫下過年的新衣,重回到他的勞動角色里,呈現一個鄉野天地里勞動男人的光芒和力量。
記憶里,父親穿著肥大的膠皮褲子,頂著陽光,劃著很肥圓的一只船,我們鄉里叫扎盆,去到門前的許家塘里,用綁了竹篙的大鐵夾夾取塘底的淤泥。那是很累的活,父親每夾滿一兩盆,一锨一锨拋到水田里,然后會把扎盆劃到門前的柳陰下,稍事歇息。他額頭上有細小的汗粒子,粉粉地覆著,在陽光下泛著亮色。待到下午三四點,母親會遞給他一碗糯米粥,碗頭上臥著兩只荷包蛋,銀元寶一樣的。父親不上岸,坐在盆沿吃,我們站在岸邊,嗅著淤泥的泥腥氣,感覺春天像在腸子里漲潮了。父親吃完,我和弟弟開工,鍋底剩下的糯米粥,母親分給我和弟弟,一人一小碗。
父親夾淤泥的日子,對于我們,也近似一個小小的節日。那些淤泥被父親拋著,以拋物線的姿勢落進水田的一頭,像缸里還沒成形的水豆腐。那些淤泥里通常裹有隔年的落進水底的菱角種,我和弟弟舉著細長的竹竿在里面找,才上岸的菱角種一般都翹在淤泥上面,極易找。找到了,勾過來,洗洗,剝開當水果吃。吃過菱角種,晚上做夢,嘴角還能嚼出甜來。
在物資依然匱乏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,不僅我們的腸胃缺乏豐富的魚肉果蔬,連土地也是,缺肥料是尋常事。那些被父親夾上來的淤泥,它們多半是腐葉和泥土的混合物,被農人們當作田地的肥料,改造土壤,播種幼苗。
在三月的中午和黃昏,我放學,穿過一大片遼闊的田野,路過開著紫花的紫云英田,常常會遇見正在犁田的農人。這些甩著鞭子吆喝著水牛的農人當中,就有父親。牛在前,父親在后,像個指揮戰役的將軍,綠葉紫花的紫云英被雪白的鐵犁掀毯子一樣掀起來。田犁過,灌上水,明晃晃的水田里倒映著云天,遇到微風,陽光在水田上像綢子起了皺。水田漚上三五六七日,紫云英腐爛了,也成了稻田的好肥料。那時我經過父親的田邊,和風煦日之下,花的香,葉的清氣,泥土的潮濕腥味,父親的汗水味,混合成鄉村三月的空氣。空氣也像是肥沃的了,整個鄉村都被這醉人的空氣喂養著。
這個時節,父親也開始漚稻種了。他拿了麻袋,頭鉆進稻倉里,挖了小半袋,扎緊口,放到許家塘里泡。三五日,拎上來,解開,伸手撈一把出來瞧,出芽了。白白的芽,像細腰身的小蟲,爬出來,在指間蠕動。水田里的淤泥已經被整成秧床了,父親腰間夾著盛了稻種的小盆,陷在水田里撒。堂哥牽著生產隊里的牛,路過水田,他看一看,牛也看一看。一秧田的陽光,一牛背的陽光。沒撒完的稻種,曬干了,去了殼,磨了來做芽稻粑粑吃,極甜,所以我每年都盼望著父親的稻種撒不完。
待早稻秧苗已經插進水田里,行行列列,排成了綠色的詩行,春光就此算是打了一個小結,退場。在母親的洗洗曬曬、燒燒煮煮之間,新一撥的農家俗事又踏進了立夏的門檻。小麥抽穗,油菜結莢,陽光有點緊鑼密鼓的熱鬧,記憶中,人間四月就是這樣在父親的雙手之間來臨的吧。
父親一樣的人
□錢紅麗
端午節那天,忽然想問候姚老一聲。一直留著老人家的微信。也不知,天上的他,可能感知到?
以往,每逢年節,老人家總是早早發來一條祝福短信,并非群發那種,一貫珍而重之。倘是端午節,便是:小錢,祝全家安康!若是中秋,他寫:小錢,祝闔家幸福!
之前,一向粗枝大葉的我,不曾有過年節編發短信的習慣。得益于姚老的潛移默化,才漸漸形成的主動問候長輩的意識。往后,便也留了心,想著一定要趕在姚老發短信之前,問候他老人家。可是,每一次皆落空。每臨節日醒來,打開手機,姚老的“祝福”總是先我一步。
姚老與我父親年齡相當。只是,他向無長輩架子,一年年地,給一個遠在異地的晚輩發著祝福短信。
借著參加副刊研究會的機會,我們得以認識,不過是一年見一次。每一次見面,宛如鄰居那么熟稔,老人家親切隨和地迎過來,父親一樣地招呼著:嗯,小錢你胖了。或者是,小錢,你上次采風文章寫得不錯……一句句家常話,一次次凸顯著老先生氣質里的赤誠質樸。末了,還要說些激賞的話。有時,在北京的他正翻看一份報紙,見副刊版面上有我文章,老先生也發短信過來,表揚肯定一番,讓我的內心涌起陣陣暖意,慢慢地,竟有一份哽咽的情緒縈繞。
所為何來?
高小文化的我父親,情感頗為粗獷,平素對待我們姐弟仨,不是抱怨,便是苛責。記憶里,我父親不曾當面夸獎過我們一句。一次,二老來我家小居。一日,父親拿過一本我新出的書,粗略翻過幾頁,非常嚴肅地搖頭道:你這文章寫得不行嘛,一個形容詞也沒有。我母親且在一旁附和:說出來你不要生氣嗷,我覺得你沒有我寫得好,我三年級時的作文,經常被老師念。
在這樣的家庭,想得一句父母的肯定,難于登天。
而菩薩一樣的姚老,連在紙媒上看見我一篇小文章,縱然隔著千里,他也要認真地肯定你一下。怎能不令人感動?這不過是他的佛心他的慈悲。
慈悲之人,內心的愛綿延無盡,時時滿溢。想必他不僅對我這個晚輩,對所有認識的人,他都不吝贊美過吧。
有一年,我們在浙江東陽采風。東陽以木雕聞名。當集合時間到,汽車發動,姚老自一家小店飛奔而出,雙手抱著一個包裝嚴實的木雕,眾人圍攏,問他買了什么寶貝。他激動地說,這個木雕是我女兒的屬相,栩栩如生……彼時,他大約七十余歲的年紀,他的寶貝女兒大抵與我年齡相近,怕也早已成家當上母親了。可是,一個做了母親的女兒,卻依然被老父親孜孜疼愛著,甚或出差千里之外,牽絆的依舊是女兒。做姚老的女兒,真是有福氣。而我,每每在外,比如參觀當地酒坊什么的,條件反射第一想到的是給父親買兩瓶酒快遞回小城。如此,一次次,形成肌肉記憶。半生往矣,并未受到過來自父親的什么禮物,也不覺有何不妥,整個人似乎置身于一種混沌狀態里。
但,那一天,當看見姚老為他寶貝女兒買到一件木雕禮物時,我何以就破防了呢?
有一年夏天,中國詩歌學會于黃山宏村舉辦國際童詩研討會,他們向我發來參會通知。不曾寫過一首童詩的我一頭霧水,惴惴不安問詢舉辦方工作人員,我一個不寫詩的人,怎么有資格去參加國際童詩會呢?組委會方才道出原委:鑒于研討會在安徽舉辦,他們原本是向姚老咨詢安徽另一家新聞媒體記者的聯系方式,姚老卻向他們極力推薦了我,給出的理由是,小錢的文章跟別人的不一樣。
這位老人,我確乎與他不曾有過深層次的交往,可是,惜才的他偏要倔強著將我推薦出去。
自十五歲進入社會,命運再也不曾發過幾張牌給我……靠著對于文學的熱愛,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回顧數次求職被拒經歷,實在艱辛。不過是,這世上,像姚老這樣的伯樂甚少罷了。
如此,姚老給予的一次次鼓勵,都是令我無比感念的。
作為一位北大人,姚老身上有著難能可貴的老派精神,他始終關心底層,一直共情于埋頭苦干之人。一次,他發短信來,說安慶市有一位工人勞模,讓我一定去采訪一下。彼時,我所在的單位風雨飄搖,早已萌生去意,但,又非長袖善舞之人,人至中年重找工作,何其艱難。一直深陷抑郁之中的人,無比恐懼外出。便向老人家借口推脫,又不便說出自己的精神狀態。過后,隔一陣,老人家又發短信來,還是規勸我應該去一趟安慶……
到底未能成行。老人家想必對我無比失望吧。
有一年,在云南采風結束后,他風塵仆仆前往另一地去采訪一位勞模……望著背著行李的老人愈走愈遠,直至消失于安檢口,實在感佩。
姚老的氣質里,完好保存著典型的知識分子風骨。榮休多年的他,不知疲倦,執意奔波,不過是對于記者這份職業的摯愛吧。
視力越來越差的我,極少翻看微信,直至去年的一日,當通過朋友圈得知老人的消息時,老人早已故去了。
去年端午,我的祝福短信又沒有搶在他之前發出。回頭算一算他故去的日期,那么,端午節時的他,已在病中了。
過后幾天,我常常情不自禁去翻朋友圈,默默讀著人們懷念姚老的文字,卻不能說出一句話,亦不能寫出一行字。
當姚老得知大限迫近,卻一如既往于節日里,向我們發著一條條祝福短信。那個病到了晚期,是極度疼痛的。老人家這是何等的超脫。他都不曾向尊敬自己關心自己的人告別一聲……每每念及,幾欲淚濕。
有一年秋,在永嘉,當我們乘船去江心嶼參觀。一船的年輕陌生人好整以暇地坐在位置上,唯獨姚老神情疲憊地站在角落里。我找著了一個空位,勸他坐下,他推辭,說不累不累。內斂的我也不知哪來的勇氣,一把抓過他的手,牽著他,穿過人群來到座位前。我不過是將他當作自己父親一樣的關心著了。老人家對我這個晚輩的關照,再也沒有機會報答了。
甲辰暮春,副刊人齊聚紹興。一日午后,情緒低落的我,獨坐于蘭亭小賣部的塑料椅上發呆,姐姐一般溫暖的陳戎老師特地前來關心:你怎么了呢?
不過是想到了姚老。這草木葳蕤的暮春,一位父親一樣的老人,再也不能與我們一起徜徉山山水水了。而我們,依然熱烈地活在世上……


 設為首頁
設為首頁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系我們
聯系我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