·天風
五六年前的一個夏日,北京龍泉寺一株千年銀杏樹下,我罩一身濃蔭,思緒散散漫漫: 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晝夜”為什么一定是時間呢。時間是時間,物是物,時間是跑來看熱鬧的,不懂痛癢,無關是非。“人事有代謝,往來成古今。”時間面前,人多卑賤啊,不知自己被時間蒙騙利用,還自作多情,物也是。可眼前這一株銀杏樹,你說它是不是時間呢。
龍泉寺正在修繕,無法進大殿,走幾步,折回來繼續看銀杏。千年的銀杏,蒼顏古貌,悲辛滋味。細觀每一片葉子,卻又蓬勃,一種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美,使人思及甘肅畢家灘26號墓出土的那套紫纈襦和緋碧裙。記得是杭州的絲綢博物館,我在那套襦裙前長時間站立。著衣中性的人,第一次對一套裙裝入迷。湊近看每一個細節,退后把玩配色,想象當年穿這套衣裳的女子,“一編香絲云撒地,玉釵落處無聲膩。”始終看不夠,臨走時,又回到襦裙前,拍下一張照片。銀杏葉似那襦裙,看不厭,使人遐想。
一直想,到深秋時節,再來樹下看黃葉紛紛,看銀杏果掉落一地,如果能撿拾一粒,也許會揣摩許久。
壬寅年八九月間,輾轉北京幾家醫院,后來在方莊住下,等一個檢查結果。以前也怕吹空調,不過不至于聞風喪膽,這次不一樣。隨身攜帶厚的羊毛披肩,一進有空調的屋子,匆忙披掛起來。如此小心,一場熱感冒還是將人放倒。昏天黑地躺兩天,忽然想該回高原了。年齡愈大,離開高原時心愈會空懸起來。乙亥年冬月,在三亞時已明確感知這一點。冬日三亞,無可挑剔,望海,觀花,坐陽臺吹風,看大鳥飛進房間。然而心終究虛空,地角天涯的黯然。直到回西北,走下飛機,呼吸到凜冽干燥的空氣,看見四周綿延的荒寒山脈,心一下明媚起來。這次亦是,逗留北京月余,漫長如年。買好機票,感冒好一些,尚有一日,決定步行去琉璃廠看景泰藍。
景泰藍展館只有我和一位女館員。女館員不遠不近地跟,有些尷尬,彼此找話。吸引人的,是展館的幾對景泰藍獅子,絢麗又嫵媚,尤其一只小獅子,蹲在墻角,項系鈴鐺,腳踩一只幼獅。那幼獅被它踩得生疼,小嘴巴洞開,正求救,甚是可愛。流連獅子左右,想肩扛一只回去。又想一女子扛一獅子在路上,吭哧吭哧,不雅觀,只好作罷。上樓,買一只景泰藍的貓頭鷹,揣在手心,往回走。
依舊步行,手機導航。走幾步,手機和人似乎都出問題。迷在路口,左右倒騰,等尋到一條熟悉出口時,一路銀杏突然相迎。
是芳城路的銀杏。銀杏樹栽植時間不長,樹只有一層樓高,葉子卻已泛黃。路邊其他樹木還是綠意蔥蘢,木槿紫薇月季尚在開花,銀杏似乎忍受不了夏季拖拖拉拉而將秋色一把捧上。那種未曾明亮的黃,摻些橙紅,自葉緣往中心過渡,仿佛一柄綠色折扇湊近火堆,不小心點著火苗,手忙腳亂,匆匆熄滅。也有幾株,葉子已全部黃透,秋天在枝杪間風生水起。
那一時夕陽已墜到樓頂,西天紅光散射,一片曼妙。朦朧的光暈里,是騎電動車回家的人,是已經打開前燈的公交車和緩慢行駛的小汽車。一天的事情尚未結束,回家的路總是匆忙。如此流動躁亂的氣息中,一樹黃葉的銀杏靜靜佇立,望過去,忽生一種“赤葉楓林落酒旗,白沙洲渚夕陽微;數聲柔櫓蒼茫外,何處江村人夜歸”的悠遠蒼茫。
有銀杏果掉到地面,撿拾一柄把玩。兩枚果子對生,仿佛一對小動物的耳朵。銀杏果又名白果,可食,入藥。如果寄住的地方有鍋灶,可以多撿幾枚,剝掉果肉,洗凈果核,平底鍋鋪一層鹽,放銀杏果,再鋪一層鹽,烤出來,慢慢吃。當然,剝銀杏果的時候,得戴手套,銀杏果有微毒,中毒了可不好。以前吃過椒鹽白果,一小碟,清供似的,只是太咸,嘗嘗味道就可以。
有一次,聽一位中醫講課,說,有老慢支的病人,平時吃點銀杏果好,但不能多吃,每天七枚最佳,做法簡單:找一個牛皮信封,裝七枚白果進去,將信封扎起,放進微波爐,加熱20秒,拿出即可食用。
忽然想,如果微波爐是通往陌生宇宙的隧道,不久之后,某個星球上的生物會收到一封古老的信,里面是七枚白果。它不知拿白果怎么辦,用爪子捏,用牙齒咬,剖開一枚,用生物放大鏡看,然后小心收起,等待破解。這個過程白駒過隙,卻又千年萬年。
【橙美文】寄給時間的信
安徽商報
張雪子
2023-05-06 10:34:12
·天風
五六年前的一個夏日,北京龍泉寺一株千年銀杏樹下,我罩一身濃蔭,思緒散散漫漫: 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晝夜”為什么一定是時間呢。時間是時間,物是物,時間是跑來看熱鬧的,不懂痛癢,無關是非。“人事有代謝,往來成古今。”時間面前,人多卑賤啊,不知自己被時間蒙騙利用,還自作多情,物也是。可眼前這一株銀杏樹,你說它是不是時間呢。
龍泉寺正在修繕,無法進大殿,走幾步,折回來繼續看銀杏。千年的銀杏,蒼顏古貌,悲辛滋味。細觀每一片葉子,卻又蓬勃,一種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美,使人思及甘肅畢家灘26號墓出土的那套紫纈襦和緋碧裙。記得是杭州的絲綢博物館,我在那套襦裙前長時間站立。著衣中性的人,第一次對一套裙裝入迷。湊近看每一個細節,退后把玩配色,想象當年穿這套衣裳的女子,“一編香絲云撒地,玉釵落處無聲膩。”始終看不夠,臨走時,又回到襦裙前,拍下一張照片。銀杏葉似那襦裙,看不厭,使人遐想。
一直想,到深秋時節,再來樹下看黃葉紛紛,看銀杏果掉落一地,如果能撿拾一粒,也許會揣摩許久。
壬寅年八九月間,輾轉北京幾家醫院,后來在方莊住下,等一個檢查結果。以前也怕吹空調,不過不至于聞風喪膽,這次不一樣。隨身攜帶厚的羊毛披肩,一進有空調的屋子,匆忙披掛起來。如此小心,一場熱感冒還是將人放倒。昏天黑地躺兩天,忽然想該回高原了。年齡愈大,離開高原時心愈會空懸起來。乙亥年冬月,在三亞時已明確感知這一點。冬日三亞,無可挑剔,望海,觀花,坐陽臺吹風,看大鳥飛進房間。然而心終究虛空,地角天涯的黯然。直到回西北,走下飛機,呼吸到凜冽干燥的空氣,看見四周綿延的荒寒山脈,心一下明媚起來。這次亦是,逗留北京月余,漫長如年。買好機票,感冒好一些,尚有一日,決定步行去琉璃廠看景泰藍。
景泰藍展館只有我和一位女館員。女館員不遠不近地跟,有些尷尬,彼此找話。吸引人的,是展館的幾對景泰藍獅子,絢麗又嫵媚,尤其一只小獅子,蹲在墻角,項系鈴鐺,腳踩一只幼獅。那幼獅被它踩得生疼,小嘴巴洞開,正求救,甚是可愛。流連獅子左右,想肩扛一只回去。又想一女子扛一獅子在路上,吭哧吭哧,不雅觀,只好作罷。上樓,買一只景泰藍的貓頭鷹,揣在手心,往回走。
依舊步行,手機導航。走幾步,手機和人似乎都出問題。迷在路口,左右倒騰,等尋到一條熟悉出口時,一路銀杏突然相迎。
是芳城路的銀杏。銀杏樹栽植時間不長,樹只有一層樓高,葉子卻已泛黃。路邊其他樹木還是綠意蔥蘢,木槿紫薇月季尚在開花,銀杏似乎忍受不了夏季拖拖拉拉而將秋色一把捧上。那種未曾明亮的黃,摻些橙紅,自葉緣往中心過渡,仿佛一柄綠色折扇湊近火堆,不小心點著火苗,手忙腳亂,匆匆熄滅。也有幾株,葉子已全部黃透,秋天在枝杪間風生水起。
那一時夕陽已墜到樓頂,西天紅光散射,一片曼妙。朦朧的光暈里,是騎電動車回家的人,是已經打開前燈的公交車和緩慢行駛的小汽車。一天的事情尚未結束,回家的路總是匆忙。如此流動躁亂的氣息中,一樹黃葉的銀杏靜靜佇立,望過去,忽生一種“赤葉楓林落酒旗,白沙洲渚夕陽微;數聲柔櫓蒼茫外,何處江村人夜歸”的悠遠蒼茫。
有銀杏果掉到地面,撿拾一柄把玩。兩枚果子對生,仿佛一對小動物的耳朵。銀杏果又名白果,可食,入藥。如果寄住的地方有鍋灶,可以多撿幾枚,剝掉果肉,洗凈果核,平底鍋鋪一層鹽,放銀杏果,再鋪一層鹽,烤出來,慢慢吃。當然,剝銀杏果的時候,得戴手套,銀杏果有微毒,中毒了可不好。以前吃過椒鹽白果,一小碟,清供似的,只是太咸,嘗嘗味道就可以。
有一次,聽一位中醫講課,說,有老慢支的病人,平時吃點銀杏果好,但不能多吃,每天七枚最佳,做法簡單:找一個牛皮信封,裝七枚白果進去,將信封扎起,放進微波爐,加熱20秒,拿出即可食用。
忽然想,如果微波爐是通往陌生宇宙的隧道,不久之后,某個星球上的生物會收到一封古老的信,里面是七枚白果。它不知拿白果怎么辦,用爪子捏,用牙齒咬,剖開一枚,用生物放大鏡看,然后小心收起,等待破解。這個過程白駒過隙,卻又千年萬年。
·天風五六年前的一個夏日,北京龍泉寺一株千年銀杏樹下,我罩一身濃蔭,思緒散散漫漫: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晝夜”為什么一定是時間呢。時間是時間,物是物,時間是跑來看熱鬧的,不懂痛癢,無關是非。“人事有代謝,往來成古今。”時間面前,人多卑賤啊,不知自己被時間蒙騙利用,還自作多情,物也是。可眼前這一株銀杏樹,你說它是不是時間呢。龍泉寺正在修繕,無法進大殿,走幾步,折回來繼續看銀杏。千年的銀杏,蒼顏古貌,悲辛滋味。細觀每一片葉子,卻又蓬勃,一種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美,使人思及甘肅畢家灘26號墓出土的那套紫纈襦和緋碧裙。記得是杭州的絲綢博物館,我在那套襦裙前長時間站立。著衣中性的人,第一次對一套裙裝入迷。湊近看每一個細節,退后把玩配色,想象當年穿這套衣裳的女子,“一編香絲云撒地,玉釵落處無聲膩。”始終看不夠,臨走時,又回到襦裙前,拍下一張照片。銀杏葉似那襦裙,看不厭,使人遐想。一直想,到深秋時節,再來樹下看黃葉紛紛,看銀杏果掉落一地,如果能撿拾一粒,也許會揣摩許久。壬寅年八九月間,輾轉北京幾家醫院,后來在方莊住下,等一個檢查結果。以前也怕吹空調,不過不至于聞風喪膽,這次不一樣。隨身攜帶厚的羊毛披肩,一進有空調的屋子,匆忙披掛起來。如此小心,一場熱感冒還是將人放倒。昏天黑地躺兩天,忽然想該回高原了。年齡愈大,離開高原時心愈會空懸起來。乙亥年冬月,在三亞時已明確感知這一點。冬日三亞,無可挑剔,望海,觀花,坐陽臺吹風,看大鳥飛進房間。然而心終究虛空,地角天涯的黯然。直到回西北,走下飛機,呼吸到凜冽干燥的空氣,看見四周綿延的荒寒山脈,心一下明媚起來。這次亦是,逗留北京月余,漫長如年。買好機票,感冒好一些,尚有一日,決定步行去琉璃廠看景泰藍。景泰藍展館只有我和一位女館員。女館員不遠不近地跟,有些尷尬,彼此找話。吸引人的,是展館的幾對景泰藍獅子,絢麗又嫵媚,尤其一只小獅子,蹲在墻角,項系鈴鐺,腳踩一只幼獅。那幼獅被它踩得生疼,小嘴巴洞開,正求救,甚是可愛。流連獅子左右,想肩扛一只回去。又想一女子扛一獅子在路上,吭哧吭哧,不雅觀,只好作罷。上樓,買一只景泰藍的貓頭鷹,揣在手心,往回走。依舊步行,手機導航。走幾步,手機和人似乎都出問題。迷在路口,左右倒騰,等尋到一條熟悉出口時,一路銀杏突然相迎。是芳城路的銀杏。銀杏樹栽植時間不長,樹只有一層樓高,葉子卻已泛黃。路邊其他樹木還是綠意蔥蘢,木槿紫薇月季尚在開花,銀杏似乎忍受不了夏季拖拖拉拉而將秋色一把捧上。那種未曾明亮的黃,摻些橙紅,自葉緣往中心過渡,仿佛一柄綠色折扇湊近火堆,不小心點著火苗,手忙腳亂,匆匆熄滅。也有幾株,葉子已全部黃透,秋天在枝杪間風生水起。那一時夕陽已墜到樓頂,西天紅光散射,一片曼妙。朦朧的光暈里,是騎電動車回家的人,是已經打開前燈的公交車和緩慢行駛的小汽車。一天的事情尚未結束,回家的路總是匆忙。如此流動躁亂的氣息中,一樹黃葉的銀杏靜靜佇立,望過去,忽生一種“赤葉楓林落酒旗,白沙洲渚夕陽微;數聲柔櫓蒼茫外,何處江村人夜歸”的悠遠蒼茫。有銀杏果掉到地面,撿拾一柄把玩。兩枚果子對生,仿佛一對小動物的耳朵。銀杏果又名白果,可食,入藥。如果寄住的地方有鍋灶,可以多撿幾枚,剝掉果肉,洗凈果核,平底鍋鋪一層鹽,放銀杏果,再鋪一層鹽,烤出來,慢慢吃。當然,剝銀杏果的時候,得戴手套,銀杏果有微毒,中毒了可不好。以前吃過椒鹽白果,一小碟,清供似的,只是太咸,嘗嘗味道就可以。有一次,聽一位中醫講課,說,有老慢支的病人,平時吃點銀杏果好,但不能多吃,每天七枚最佳,做法簡單:找一個牛皮信封,裝七枚白果進去,將信封扎起,放進微波爐,加熱20秒,拿出即可食用。忽然想,如果微波爐是通往陌生宇宙的隧道,不久之后,某個星球上的生物會收到一封古老的信,里面是七枚白果。它不知拿白果怎么辦,用爪子捏,用牙齒咬,剖開一枚,用生物放大鏡看,然后小心收起,等待破解。這個過程白駒過隙,卻又千年萬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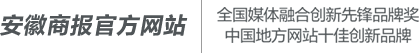
 設為首頁
設為首頁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系我們
聯系我們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