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年起,“高齡農(nóng)民工”話題開始進(jìn)入公共視野,也引起了安徽師范大學(xué)社會(huì)工作與社會(huì)學(xué)系副教授仇鳳仙的關(guān)注。2017年,她開始著手主持研究“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”相關(guān)課題,歷時(shí)5年,于2022年結(jié)題,并寫成《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可持續(xù)生計(jì)研究》一書,將于今年6月份出版。
在這項(xiàng)課題里,她通過大量走訪、發(fā)放數(shù)千份問卷以及面對(duì)面訪談,對(duì)中國(guó)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群體進(jìn)行了深入細(xì)致的調(diào)研和分析。她對(duì)每一位被訪的農(nóng)民工都印象深刻,心懷共情,但落筆時(shí),又保持著學(xué)者的嚴(yán)謹(jǐn)和冷靜,務(wù)求每一個(gè)數(shù)據(jù)都有出處。
在她看來,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離開故土進(jìn)入城市務(wù)工,通過勞動(dòng),當(dāng)然地獲得了經(jīng)濟(jì)收入上的比較利益,同時(shí)也失去了很多,尤其是當(dāng)“代際跨越”這一初衷未能實(shí)現(xiàn)時(shí),他們的人生被添上了一抹悲涼的色彩。
這本書,和她2022年4月出版的《傾聽暮年:李村老人日常生活實(shí)踐研究》,以及她正在籌劃的“大國(guó)小工”選題,將構(gòu)成“農(nóng)村老年三部曲”,她希望以此有助于深入審視農(nóng)村社會(huì),并為基層社會(huì)治理提供經(jīng)驗(yàn)資料。

在農(nóng)村問題研究領(lǐng)域深耕多年,她努力在內(nèi)心保持一份“人文”的柔軟,渴望在學(xué)者身份之外,嘗試去做一個(gè)“傾聽者”和“講述者”,關(guān)于第三本書,她準(zhǔn)備在大量訪談的基礎(chǔ)上,多一點(diǎn)類似于“口述史”那樣的現(xiàn)場(chǎng)感,“不一定非得多么具有學(xué)術(shù)性,而是寫成我自己喜歡的樣子。”
他們像鳥,在不同城市間遷徙
仇鳳仙先后訪談了200多個(gè)農(nóng)民工,籍貫涉及四川、山東、河南、內(nèi)蒙古、云南和安徽等多地。這里面有不少是在工地旁或者馬路邊偶遇的,她一眼就能看出,那些三三兩兩聚在一起的人,就是她的研究對(duì)象。
這樣的訪談隨機(jī)、突發(fā),雙方不會(huì)有任何提前的安排,讓人覺得更可靠。
多年的田野調(diào)查,讓仇鳳仙擁有很多經(jīng)驗(yàn),她能讓那些心懷戒備的陌生人打開話匣,向她傾訴人生的際遇。她在為上一本書《傾聽暮年》做調(diào)研時(shí),遠(yuǎn)遠(yuǎn)看到曬場(chǎng)上閑坐的老人,就湊過去,坐在臟兮兮的小板凳上和他們拉家常,慢慢的,周圍的老人們都圍了過來,話題完全打開。
2018年,她去昆明開會(huì),在路邊偶遇幾個(gè)當(dāng)?shù)剞r(nóng)民工,她就站在那和他們聊,一聊就是幾個(gè)小時(shí)。農(nóng)民工們平均年齡50歲,不會(huì)說普通話,雙方連比帶劃,很是費(fèi)勁,但卻給了仇鳳仙很多鮮活的第一手資料。
那次街頭訪談,讓她了解到云南當(dāng)?shù)剞r(nóng)民工的生計(jì)比她想像的還要差。云南偏遠(yuǎn)山區(qū)耕地少,以山林地為主,為了保護(hù)環(huán)境,山林地的開發(fā)和利用又有著諸多限制,這樣一來,村民家中的生計(jì)來源更少,被迫出來打工。“和土地、自然的那種長(zhǎng)期依存的關(guān)系被割斷了,這是他們進(jìn)城務(wù)工的主要原因,打工收入也不高,但遠(yuǎn)比在家鄉(xiāng)要好,所以他們不愿意回去。在云南和四川等地,這樣的情況很多。”
她在蕪湖火車站遇到過一位50多歲的東北人,在蕪湖三橋建設(shè)工地務(wù)工,橋修好了,他要去往另一個(gè)城市尋找新的工作。
仇鳳仙覺得他像候鳥,在不同城市間遷徙。
他告訴仇鳳仙,十幾年前,東北的工作很好找,但現(xiàn)在不好找了,最主要的原因是限煤,到了冬天,高污染的工廠全關(guān)了,最先失去工作的就是農(nóng)民工。
仇鳳仙覺得有點(diǎn)“漲知識(shí)”:不和他聊,還真不知道這種季節(jié)性的生產(chǎn)模式,蕪湖就不存在這種情況。
她還在訪談中見識(shí)到了這位農(nóng)民工的樂觀豁達(dá)。
她問:“你年齡大了,總不能老這樣在外面打工吧。”東北人瞅她一眼:“我才五十多歲,算什么大呀。”
她又問:“你孩子也都不在家,就剩老伴在家,種著幾畝地,萬一她生病了怎么辦呢?”東北人答:“要是大病我就回去,沒大病就隨她在家怎么弄,人不能活活被病死呀。”
2019年12月,仇鳳仙和同事許云云老師去西安開會(huì),她沒坐高鐵,而是選了綠皮火車,火車上有很多返鄉(xiāng)的農(nóng)民工,都往西邊去。
她帶了100多張調(diào)查問卷,卷子上列了70多道選擇題,包括“外出務(wù)工時(shí)長(zhǎng)”“收入情況”“眼下最關(guān)心最擔(dān)憂的事”“干到什么時(shí)候退休”“將來有什么打算”等。火車開起來,她就挨個(gè)發(fā),十幾份問卷發(fā)出去后,引來不少農(nóng)民工的注意,他們圍過來,紛紛伸手要問卷。
這個(gè)時(shí)候,乘務(wù)員過來制止。
為了能在這趟綠皮車上做調(diào)查,仇鳳仙提前做了很多準(zhǔn)備,打印了情況說明,找學(xué)校蓋了章,還帶上了工作證,來表明自己是有單位的人,是做調(diào)研的。
她把這些材料拿給乘務(wù)員看,沒用,乘務(wù)員告訴她,“我只認(rèn)鐵路部門的批文。”
問卷發(fā)放被中止了,仇鳳仙想和農(nóng)民工們聊天,也被制止,乘務(wù)員讓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,“如果再不聽勸,就要叫乘警了。”
“他們看上去很蒼老,硬損傷很多”
問卷調(diào)查從2018年12月份開始,中間因故中斷了一段時(shí)間,2020年又拾起來做,做了兩年多,2022年結(jié)束時(shí),共收集了2500份。
被訪者分布在全國(guó)各地。
仇鳳仙帶的學(xué)生,有不少家在外省,放假時(shí),她就讓學(xué)生帶回老家,在當(dāng)?shù)刈鰡柧碚{(diào)查。
有個(gè)重慶的女學(xué)生叫覃元林,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在安徽省一高校工作了,春節(jié)回家時(shí)她帶了400份問卷,全家人幫忙,在當(dāng)?shù)匕ぜ野羯祥T發(fā)放,過了一個(gè)很特別的春節(jié)。
還有一年暑假,女學(xué)生高慎香回老家山東做了500份問卷調(diào)查,她騎著小電驢,跑了很多村子,曬得漆黑。仇鳳仙讓她做完一個(gè)問卷調(diào)查給人家一塊錢,“表示一下心意”,高慎香就拿著手機(jī)找對(duì)方要收款碼,人家死活不要,后來,她再上門發(fā)問卷時(shí),就背一袋子一元硬幣,填完問卷,就硬塞給人家一枚。
像在暗房里沖洗膠片底片一樣,中國(guó)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的整體輪廓,在這2500份調(diào)查問卷里慢慢顯現(xiàn)出來。
問卷顯示,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的農(nóng)民工占83.85%,外出務(wù)工年限超過20年的占41.22%,外出務(wù)工20年以下16年以上的占10.98%,沒有和雇用單位簽訂勞動(dòng)合同的占64.24%,女性農(nóng)民工占25.72%,在健康自評(píng)中認(rèn)為自己沒有大病的占62.65%,對(duì)未來抱有樂觀的人占40%,“這是因?yàn)樗麄兊纳眢w狀況尚可,再加上家里有其他經(jīng)濟(jì)來源的支持,讓他們的壓力不會(huì)太大。”
但實(shí)際上,被訪者的健康狀況都不太好。仇鳳仙總結(jié)認(rèn)為,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在健康狀況方面擁有一些共性:比如他們外表看上去都很蒼老,大都比實(shí)際年齡要老上幾歲甚至十幾歲;比如身體的硬損傷很多,肩膀、胳膊、腰、腿這些部位疼痛是普遍現(xiàn)象;還有在高污染環(huán)境里工作導(dǎo)致的傷害,有位被訪者長(zhǎng)期在上海一家帆布包加工廠里工作,空氣中充斥著刺鼻嗆人的味道,最終他得了紅斑狼瘡。
被訪農(nóng)民工基本上沒有談及精神生活。問卷里有一道題涉及到他們的社會(huì)關(guān)系網(wǎng)絡(luò),“你心情不好的時(shí)候向誰傾訴?”結(jié)果顯示,向家人和親友傾訴的占74.54%,選擇向打工時(shí)認(rèn)識(shí)的當(dāng)?shù)厝藘A訴的僅占8%。

清晨的勞務(wù)市場(chǎng),工友們聚在一起等活來
上世紀(jì)70年代出生的農(nóng)民工,年齡在40多歲到50多歲之間,這個(gè)年齡段的農(nóng)民工,存錢的幾乎沒有,因?yàn)樗麄兊淖优丛谀顣吹搅私Y(jié)婚成家的時(shí)候,農(nóng)村的高價(jià)彩禮是一個(gè)很大的負(fù)擔(dān),他們的勞動(dòng)所得,全都要付出給家庭,“這個(gè)結(jié)果也符合我們學(xué)術(shù)界關(guān)于儲(chǔ)蓄的U型理論,中年人,四五十歲這一段,儲(chǔ)蓄是處于最低點(diǎn)的。”
不同年齡層的農(nóng)民工,對(duì)未來的預(yù)期和養(yǎng)老的規(guī)劃也不一樣,這一點(diǎn)在問卷里體現(xiàn)得特別明顯。上世紀(jì)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,如今已經(jīng)六七十歲了,他們知道子女和孫輩都靠不住,靠山山倒,靠水水流,開始有了養(yǎng)老的意識(shí)和行動(dòng),開始主動(dòng)存錢,“我問那些在社區(qū)做保潔、綠化的老人,他們說工資是日結(jié),一天能掙80塊錢,他們把這錢都留給自己。新農(nóng)合一個(gè)月150塊錢,一天掙80塊錢對(duì)他們來說已經(jīng)是一筆很大的收入。”
2020年仇鳳仙訪談過一位姓項(xiàng)的老人,老家在六安,當(dāng)時(shí)已經(jīng)73歲,在合肥一家養(yǎng)老院做護(hù)工,包吃包住,月工資4500元左右。老人告訴仇鳳仙,他老伴患有白癲風(fēng),他得出來掙錢給老伴治病,“我問單位有沒有給他買保險(xiǎn),他說那是城里人才能有的,能掙點(diǎn)錢在身上就不怕了。”“他們想的很簡(jiǎn)單,為自己晚年生活多一點(diǎn)經(jīng)濟(jì)儲(chǔ)備,心里就會(huì)安穩(wěn)些。”
“我們和他們不是一樣的人”
怎么界定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?學(xué)術(shù)界的定義是,凡在上世紀(jì)70年代及以前出生、并在上世紀(jì)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外出務(wù)工人群,都可以視為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。按這個(gè)算法,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里年齡最小的在40多歲,年長(zhǎng)的約六七十歲甚至更老。
仇鳳仙曾訪談過一位70多歲的女農(nóng)民工,年輕時(shí)去上海浙江等地打工,不停換廠換工作,遇到農(nóng)忙時(shí),就抽空回來一趟,忙完農(nóng)活回去繼續(xù)打工。年齡大了后,回到老家,仍然打零工,后來找到一份環(huán)衛(wèi)保潔的工作,一個(gè)月1800元,她很滿足。
老人回憶說,在城市里打工,最讓人難受的就是“怕被人看不起”,她吃飯時(shí)專找路邊的小攤,那里是農(nóng)民工比較聚集的地方,平時(shí)幾乎不和城里人搭訕,“我們和他們不是一樣的人。”
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外出時(shí),城鄉(xiāng)二元結(jié)構(gòu)尚未松動(dòng),城里人和農(nóng)村人之間仍然隔著一層無形的身份壁壘,這也導(dǎo)致農(nóng)民工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定位為城市的邊緣群體。他們擔(dān)心遇到城里人的喝斥,擔(dān)心被當(dāng)作小偷一樣防備,所以盡可能將自己與城市隔絕開來,城市里的公園、商場(chǎng)、圖書館、娛樂場(chǎng)所,和他們沒有任何關(guān)系,唯一將他們與城市連結(jié)起來的,就是工作,他們只在因?yàn)猷l(xiāng)土屬性而構(gòu)建起來的圈子里活動(dòng),這也是他們唯一的社交圈。
但是,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身上,又無一例外地背負(fù)著“代際跨越”的使命。
仇鳳仙訪談過一位熟人,出生在上世紀(jì)60年代末,家在皖北農(nóng)村,是村里唯一一個(gè)高中生,上世紀(jì)90年代,他成了村里第一批外出務(wù)工的一員。外出務(wù)工前,因?yàn)檎也坏介T路,他找到一個(gè)遠(yuǎn)房親戚,給人家送了禮,然后被帶去了上海浦東。
浦東正在大開發(fā),他在建筑工地上找到了活,當(dāng)時(shí)全國(guó)平均月收入不過300元至500元,他一天能掙10塊錢,覺得太好了。但是活太苦太累,受不了,他在工地上攪拌混凝土,胳膊每天都是腫的。
浦東建設(shè)完了,他又隨別人去了廣東,進(jìn)過工廠,在工地上呆過,多年下來,腰疼、腿疼,落下半身毛病。
那些年,他愛人一直在家?guī)Ш⒆樱隽羰嘏浴K鷲廴苏f:我負(fù)責(zé)掙錢,你負(fù)責(zé)把孩子帶好,不用管其他的。
為了多掙錢,他盡量不回家探親,因?yàn)椤盎乩霞乙焚M(fèi),還要給老人們親戚們帶禮物,回家一趟支出太大。”遇到午收秋收,農(nóng)民工大量返鄉(xiāng),老板會(huì)高價(jià)留人,他就留下來,最長(zhǎng)時(shí),他有三四年都沒回家。
某年暑假,愛人帶著孩子去和他團(tuán)聚。有一天晚飯后,他帶著家人去爬工地附近的一座小山,爬到山頂,四面開闊,他們看到了夜色中的城市在漫無邊際地鋪展,他感慨地說,唉,這眼前的萬家燈火,將來有哪一扇窗戶里的燈光,是我兒子的呢?
仇鳳仙覺得這個(gè)農(nóng)民工“很有情懷”,“他從來沒為自己打算過,想的只有孩子,這也是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外出的最大動(dòng)力。”
他的兩個(gè)兒子,后來都考上了大學(xué),在城市里安家立業(yè),年過半百的他,現(xiàn)在仍然在打工,替孩子還房貸,但對(duì)他來說,這已經(jīng)是“甜蜜的負(fù)擔(dān)”。
這位農(nóng)民工在外打拼了30年,終于實(shí)現(xiàn)了“代際跨越”,但這樣的例子,少之又少。
“代際跨越”之痛
仇鳳仙用“4D”來形容第一代農(nóng)民進(jìn)城就業(yè)的工作類型。4D分別是Dirty(臟)、Danger(危險(xiǎn))、Damage(損傷)和Difficult(就業(yè)困難)。
除此之外,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還較多地受到國(guó)家相關(guān)政策的影響,一旦有風(fēng)吹草動(dòng),就得立馬返鄉(xiāng)。
資料顯示,從流動(dòng)政策變遷的角度來看,改革開放以來我國(guó)農(nóng)村的社會(huì)流動(dòng)可以細(xì)分為松綁期、調(diào)控期和積極引導(dǎo)期三個(gè)階段。
1978年~1988年,國(guó)家逐漸取消對(duì)農(nóng)民進(jìn)城開店、務(wù)工經(jīng)商的政策限制,由此形成了1989年的第一次“民工潮”。
1989年~1999年,為了減少“民工潮”對(duì)城市的沖擊,各地采取嚴(yán)格控制措施,農(nóng)民外出務(wù)工勢(shì)頭減緩。1992年后,為增加農(nóng)民收入,國(guó)家又開始放寬對(duì)農(nóng)民進(jìn)城務(wù)工的限制,由此出現(xiàn)了1992年的第二次“民工潮”和1994年的第三次“民工潮”。1990年代中后期,由于農(nóng)民進(jìn)城務(wù)工、城鎮(zhèn)新增勞動(dòng)力就業(yè)、下崗失業(yè)人員再就業(yè)“三峰疊加”,一些城市對(duì)農(nóng)民工再次采取限制措施。
在這樣的大背景下,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面臨著“經(jīng)濟(jì)吸納、社會(huì)排斥”的尷尬局面,這使得他們長(zhǎng)時(shí)間成為游離于城市與農(nóng)村之間的邊緣群體。
時(shí)代的變遷,也清晰地勾畫出不同代際的農(nóng)民工的命運(yùn)線條。“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是以‘生存—經(jīng)濟(jì)’預(yù)設(shè)為條件的外出務(wù)工邏輯,是為了解決生計(jì)問題,他們掙的錢,都要用來接濟(jì)家庭開支,尤其是子女的成長(zhǎng)。到了第二代農(nóng)民工,他們都是1980年以后出生,屬于發(fā)展自我型的,他們掙了錢,很少給家里,大多都用來改變自身的處境。到了第三代,是00后了,他們已經(jīng)越來越多地融入了城市,成為新型工人和城市新市民的一部分。”
改善家庭經(jīng)濟(jì),實(shí)現(xiàn)“代際跨越”,幾乎是所有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的夢(mèng)想,但結(jié)果卻不盡如人意。
仇鳳仙在調(diào)查和訪談中發(fā)現(xiàn),拼命干活,拼命壓縮自己的消費(fèi)空間,是農(nóng)民工們積攢財(cái)富的唯一方式,“像上世紀(jì)90年代,一個(gè)農(nóng)民工一個(gè)月能掙兩百多,省吃儉用,刨去少得可憐的開支,能寄回家兩百塊錢,這可是很大一筆錢,當(dāng)?shù)厣w一套大瓦房要四五千,他攢上兩三年就能蓋上一套了。”
但想要實(shí)現(xiàn)“代際跨越”,則要艱難的多,很多農(nóng)民工的子代,命運(yùn)并沒有改變,仍然陷在原地。
和“舉家隨遷”模式不同,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大多屬于個(gè)體流動(dòng)模式,他們外出務(wù)工后,孩子成為留守兒童,“由于親情缺失,缺少陪伴、引導(dǎo)和教育管教,孩子很難養(yǎng)成好的學(xué)習(xí)和生活習(xí)慣,走入社會(huì)后,競(jìng)爭(zhēng)力比較弱,社會(huì)化韌性很差。”
仇鳳仙想起2018年的一部紀(jì)錄片《三和人才市場(chǎng)》里的“三和大神”,“那里面拍攝的靠打日結(jié)工生存、干一天玩三天的新生代農(nóng)民工,有很多就是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的孩子。”
讓他們工作是最好的關(guān)懷
在調(diào)研中,面對(duì)“將來有什么打算?”這一問題,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中最多的回答是:哪有什么打算,干到干不動(dòng)時(shí)生病了就不干了唄。
兩年前,仇鳳仙在一篇文章里呼吁給農(nóng)村老人多提供一些好的工作機(jī)會(huì),結(jié)果被一位專家批評(píng)說“沒有人文情懷”,專家說,他們要休息,你卻還讓他們?nèi)スぷ鳌?/p>
仇鳳仙覺得,很多人并不了解農(nóng)村,不了解農(nóng)村老人的真實(shí)處境,讓他們休息,誰來給他們提供經(jīng)濟(jì)支持?工作恰恰是對(duì)他們最大的關(guān)懷。
她調(diào)研過的一位老人,75歲了還在建筑工地上打小工,正規(guī)的建筑工地進(jìn)不去,就在鄉(xiāng)村里幫私人蓋房子,一天能掙100多塊錢。
對(duì)農(nóng)村老人來說,他們沒有退休的概念,也沒有機(jī)會(huì)可以退休,只要活著,只要能動(dòng),就總要?jiǎng)谧鳌?/p>
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已經(jīng)或正在步入老年,他們的未來會(huì)怎樣?沒有人能給出一個(gè)讓人安心的答案。
但仇鳳仙還是對(duì)此抱以樂觀,她在調(diào)研中感覺到,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很少有成為城市人的想法,他們和鄉(xiāng)土的牽絆很深,也從未真正脫離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,當(dāng)他們?cè)诔鞘欣锸スぷ鳈C(jī)會(huì)后,最可能的選擇是,重新回到故鄉(xiāng)。
“我覺得政府首先應(yīng)該在制度層面上共建一個(gè)老年友好型社會(huì)。第二個(gè)就是生計(jì)落腳點(diǎn)的問題,他們?cè)缤硪氐睫r(nóng)村,不如提前在農(nóng)村搭建能容納他們的空間,比如在鄉(xiāng)村振興過程中,安排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返鄉(xiāng)后的生計(jì),讓他們力所能及參與鄉(xiāng)村建設(shè),并通過勞動(dòng)獲得報(bào)酬。他們?cè)谕鈩?wù)工多年,受過良好的訓(xùn)練,有專長(zhǎng),有見識(shí),一定能夠發(fā)揮作用。”
(安徽商報(bào)融媒體記者 祁海群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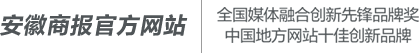
 設(shè)為首頁(yè)
設(shè)為首頁(yè)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(lián)系我們
聯(lián)系我們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