烏鎮是從天上掉下來的。
遠遠望見桐鄉的餐館時,暮色已躲進萬家燈火的背后,恍若深海湛藍的臂彎,將那茸茸薄荷香的痱子粉,迷漫著撲來,有一雙柔軟而不離不棄的母親的手,執拗地攥住嬉笑而掙扎的孩童,涂了一身清涼。
幾位年少的旅伴早早逃離餐桌,神神秘秘躲在梅雨的屋檐下,竊竊私語烏鎮的事。見我出了餐廳,干練的女領隊說:“去不去烏鎮?”當然,那我還在餐廳故意消磨時光呢。她們跟車講好了,湊了14個人,每人100塊,半小時車程,天上就掉下個烏鎮了。
江南的雨,像初戀的女孩,纏綿,溫柔,捉摸不定,但那情緒是純而又純。
江南是位女子,母性的 ,女兒性的。
雨是漫天而來的,卻無放縱與驕矜。沒有傘的游子很多,卻沒有抱怨。什么樣的母愛與戀情,只要純潔,就足夠純粹著,于我已是一生一世的奢華;而那奢華著的瑰麗,又足夠用來珍藏,遠觀而不可褻玩。
傘依然濕透了,梅雨順著北方的傘骨,滑滑地墜落著江南玲瓏的珠璣。膝下的褲腳自然早已濕透,讓行者牽絆了南國的流連,將北國的陽剛溶解作柔情陷落在雨簾之中,教人從哪里自拔。
江南的繾絹是無以掙脫了,第一次和第一百次來江南的旅人,只有融化,像一粒冰一片雪融化在江南之夜。
迷失在烏鎮的旅人,多半如我微醺,一同或獨自淺醉在雨巷的石板路上。
意趣的相投,會遇上志同道合的旅伴,哪一個想看想拍想買什么,另外的人就都愿意。這次有濤弟,一位經典的北方男,有些江南的精致與細膩,比如白皙,比如金絲眼鏡,以及眉清目秀。玉兄則不然,有著溫潤的名子,卻是典型的北方硬漢,濃眉重目,面如青銅,幽默果敢卻也隨和,不高興時也呵呵地笑得出。
我是不同了。不帥也沒城府,屬于折中的一類,相處久了可能給人由衷的感覺,適合團隊而不適合自己,難得孤獨,竟也常無由地孤獨起來,看上去與眾不同著。
我的旅行也因此沒有城府,好像不配做一個外地人,不是來旅游的,倒像個土生土長的本地人。我滿眼都是風景,是被風景融化了,丟了靈魂,才無可奈何地出神入化。故,喜歡旅游,喜歡成為那里的,一個又一個地方的本地人,并與所有風景同在。
烏鎮小巷,與周莊不同,盡管一樣的是夜,是雨,是小橋流水,卻因烏鎮巷子的雨,這樣切切地要讓北人在江南的溫潤里,融化靈魂深處的堅冰吧。
這烏鎮的小巷,刪繁就簡,只剩了自在的旅人,想怎么走就怎么走,愛怎么停就怎么停。原來是多好的風景都不重要了,自由著,和愿意同在的人同在,便是最好的行程。
(成岳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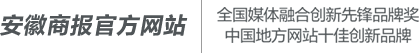
 設為首頁
設為首頁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系我們
聯系我們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