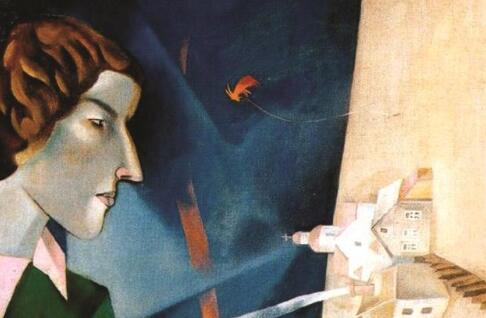2月2日,是第28個世界濕地日,今年的主題是“濕地與人類福祉”。
正值寒冬,大量候鳥自遙遠的北方而來,在安徽濕地棲息越冬。一群東方白鸛停留在樅陽菜子湖,鳥類攝影師溫躍東按動相機快門,記錄下它們佇立在淺灘中的身影。天地遼闊,大鳥雪白的頭頸和黑色的羽翼分明,寒冬的菜子湖也顯得生機無限。

溫躍東
溫躍東拍鳥已經有31年了。一只飛鳥被鏡頭記錄下的只是生命的一瞬,除了拍一張好照片,溫躍東更關注它們照片之外的命運。多年來,他的鏡頭里出現過863種鳥的身影,他也記錄并感受濕地等鳥類棲息地的變化。
遷徙中的黑鸛
自由又自信:候鳥的世界吸引他拿起相機
在萬米高空飛翔,是什么樣的感覺?小天鵝肯定知道。
1992年,一位媒體朋友邀請溫躍東一起去升金湖,那是他第一次拍鳥。“調休了兩天,開車趕到升金湖,剛到那就被震撼了。”
冬天的升金湖萬鳥翔集,大雁、灰鶴、白鶴、小天鵝、白頭鶴……到處都是鳥。當時他只有一臺美能達膠片相機,一個28-70mm的鏡頭,對著鳥群一直按快門,四卷膠卷20分鐘就拍完了。
“也沒有望遠鏡,膠卷拍完了就站在湖邊大壩上看。一會飛來一群大雁,一會飛來一群灰鶴,一會飛來一群小天鵝……看不夠,人從鋼筋水泥的城市走出來,與水鳥同處一個開闊的世界,那種感覺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。”
成群的小天鵝從天空飛過,它們擁有極強的飛行能力,從幾千公里外的西伯利亞靠翅膀無數次的扇動來到安徽,飛行高度能達到1萬米。“第一次這么近的距離看小天鵝,那么漂亮、優雅,自由自在,無拘無束。”

中華秋沙鴨
溫躍東就是在那個時候愛上了拍鳥,一拍就是31年。從膠片相機到數碼相機,到今天的“長焦大炮”,他先是跑遍了安徽,又追尋著各種飛鳥跑遍了全國,甚至遠赴海外。云南氣候溫暖,鳥種多,退休以后,他甚至在云南也安了家。
他把拍鳥當做一種養生,一段時間不拍就難受。他不“刷鳥種”,更癡迷用鏡頭記錄它們在自然中靈動的身影。為了拍一張心儀的照片,翻山越嶺、長時間守候都是家常便飯。
火尾綠鹛有著紅色的尾巴和一身綠色的衣裳,是云南怒江的“明星鳥”,也是很多拍鳥達人的“夢中情鳥”。它生活在海拔2400米以上的山區,個頭如麻雀大小,非常難拍。
溫躍東連續拍了三年,第三年他在火尾綠鹛常出現的山坡對面尋找角度,“守枝待鳥”等了三天,終于等到了一道綠光飄逸而至。快門傾瀉,火尾綠鹛佇立和起飛的瞬間被定格。“那種忽然到來的幸福,讓長時間等待的寂寞化為烏有,拍完回家路上都是哼著小曲的。”

火尾綠鶥(攝于云南)
記錄候鳥遷徙:一場為生存而戰的苦旅
“歷經重重危機后的數千里旅行,只為了一個目的,生存……候鳥的遷徙是為生命而戰。”紀錄片《鳥的遷徙》中曾這樣描述候鳥的遷徙,看似風花雪月的旅行其實是以命相搏的艱辛旅程。
溫躍東用鏡頭記錄候鳥的遷徙。2014年冬天,在霍山一處濕地,一只體型健壯的小天鵝引起了當地鳥友們的注意。相比別的小天鵝,它的個頭明顯更大一些,身上還有繁殖地科學家安裝的環志—516X。溫躍東聞訊趕來,拍下了它在安徽棲息越冬的美麗身姿。后來經林業部門調查發現,516X竟然來自遙遠的北冰洋沿岸亞馬爾半島,距離安徽直線距離達6000多公里。溫躍東感慨不已,“它要躲避城市、天敵、雷雨區等等,很可能飛越了1萬多公里才來到安徽。這一路上要經過多少艱險,令人難以想象。”
能夠平安抵達,已是極大的幸運。2021年9月,一只黑臉琵鷺亞成鳥佩戴著衛星定位裝置由韓國起飛,跨過黃海抵達中國長江出海口。按傳統路線,它應該沿海岸線南下,經江蘇、浙江、福建、廣東等地,去往海南、臺灣、香港等更溫暖的南方越冬。但當年12月16日,它卻在大理洱海附近被鳥友發現。由于目標偏差太大,它也成了云南黑臉琵鷺的首次記錄。

小天鵝516X
得知消息后,溫躍東和鳥友趕到洱海,用鏡頭記錄下這只黑臉琵鷺在洱海覓食、生活的珍貴畫面。溫躍東推測,作為一只亞成鳥,這只黑臉琵鷺缺乏長途遷徙經驗,應該是在長江口被去鄱陽湖越冬的“近親”白琵鷺帶偏了路線而迷路,獨自沿長江逆流而上,穿越2600多公里才到了大理。
雖然它沒能與家人一起抵達越冬地,但洱海食物豐富,溫躍東和鳥友們都希望它能熬過寒冬。它最終還是不幸夭折,令人十分痛心。翻閱照片和視頻,溫躍東發現,這只黑臉琵鷺身上衛星定位器的繩索一端一直拖在水里。“可能是韓國科學家安裝定位器時繩索過長或后來松脫,黑臉琵鷺身上的繩索一直是濕的,大理冬天的夜晚氣溫比較低,它或因失溫而夭折。”
溫躍東把它最后的影像編制成短視頻,希望更多的人知道它的故事。“科研工作幫助我們更好地保護鳥類,也希望科研人員做環志的時候更多考慮它們遷徙中可能遇到的風險。”
遷徙中的東方白鸛
珍惜相遇:因為拍鳥而愛鳥
溫躍東先后擔任鳥網論壇安徽版和云南版的版主,在圈里被不少鳥友稱作“大神”,不僅僅是因為他拍過很多“大片”。他花大量的時間研究鳥,它們從哪里來,到哪里去,怎樣生活,“比拍鳥還要有意思。”很多鳥友遇到不認識、不了解的鳥,都會向他請教。
去年開始,他把自己拍攝的鳥類影像制作成短視頻發在視頻號里,帶大家傾聽深山里宛若天籟的鳥鳴聲,了解一種看似尋常的小鳥,講述候鳥長途遷徙的故事……希望通過照片和短視頻,讓更多的人關注“大片”之外鳥兒們的生存境遇。
他拍鳥總會自帶一卷小繩子,把遮擋鏡頭的樹枝、草葉仔細捆扎好,拍攝完再恢復原樣。“因為拍鳥所以愛鳥,拍鳥不能驚擾鳥,不要傷害鳥。現在越來越多的鳥友有這樣的意識。”

長尾闊嘴鳥(攝于云南)
在他看來,隨著各項保護措施落地,安徽濕地生態環境整體越來越好,這些年能夠看到的鳥類種類和數量也更多了。
2014年,有攝影愛好者在霍山拍攝到中華秋沙鴨,也是“國寶鴨”近年來首次在安徽出現。此后,溫躍東長期關注中華秋沙鴨在安徽的活動規律和棲息地水質。“中華秋沙鴨被稱作‘生態試紙’,近年來中華秋沙鴨陸續在安徽多地亮相,說明這些地方的生態環境越來越好。”
人們生態保護意識不斷增強,也讓人與鳥之間的關系更加和諧。2019年,一只白鶴幼鶴降落在霍山東淠河,因為體力不支幾乎無法站立。溫躍東和鳥友輕輕掀開它的翅膀,發現翅膀根紅腫嚴重。“它可能是在繁殖地出生比較晚,幾千公里一直跟著父母拼命飛行,到了這里實在飛不動了。”白鶴一般在鄱陽湖集中越冬,霍山已經離它的目的地不到200公里。

蓑羽鶴(攝于內蒙古)
溫躍東和鳥友們向當地林業部門匯報后,又向周邊村民廣泛宣傳,請大家不要傷害它。但十多天后,這只幼鶴還是被發現趴在河灘上不幸夭折,瘦得皮包骨頭。“沒想到給它投喂食物,心里特別難過,也很自責。”
2020年11月,霍山再度迎來白鶴“小客人”。在單龍寺附近有村民發現一只落單的白鶴亞成體。(安徽商報2020年11月27日曾報道)鳥友張紅兵和旌陽夫婦一邊向鎮政府匯報,一邊聯系了遠在云南的溫躍東。大家第一時間行動起來,對它進行保護救助。
這只小白鶴被取名“單丹”,看起來身體狀況還不錯,專家認為,如果它能熬過寒冬,就有機會重回大部隊。為了防止悲劇重演,單丹得到了充足的食物投喂,政府部門、村民、學校師生、志愿者持續關注它的狀況,合肥安居苑小學的孩子們還為單丹捐款,給它買食物。在大家的呵護下,單丹慢慢長大。“飛起來非常有力量,看起來很健康。”
遷徙中的白鶴
單丹熬過了寒冬,第二年春天的一天,一群白鶴北飛經過,它順利跟上了大部隊,重回鶴群。
故事有了美好的結局,單丹卻留在了大家的心里,很多人記得單龍寺曾經來過一只小白鶴。每年冬天,白鶴遷徙經過霍山,溫躍東總會想起單丹。“再回來,它就是一只成年鶴了,也許已經拖家帶口了。”
(安徽商報融媒體記者 劉媛媛 實習生 楊顏鈺霆/文 溫躍東/攝)


 設為首頁
設為首頁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系我們
聯系我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