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這個秋,從一場風寒開始,是否息止于安寧,不得而知。這似乎暗合了秋的意韻——有幾分離索、幾分傷逝、幾分不舍……雖然,秋的另一面,是花團錦簇的盛極之況,是顆粒歸倉的殷實與歡騰。
于我,只想取它安靜、內斂的一面。在這個秋的年紀,有這樣秋的心境,應是正理。
二
于是,從艱深的“深宅大院”走出,不至于歡天喜地,倒是淡然如桌面的綠茶,自在沉浮;如碧空中棉花糖的白云,慷慨,大朵大朵的,疾行,像有牧人趕著。無辜的藍天、白云,心碎,現出世界原初的純凈模樣。
于是,一切喜愛的事情,從秋天開始計時吧——不是嗎?此刻,繁華,正當時;美好,正當時;歸納與綰結,也正當時。
三
空氣是清爽的,不油膩,不黏稠,卻也不失夏的柳綠花紅。
冷熱均衡,干濕適度。穿兩件衣服的感覺真好:一件,汗津津的;三件以上,太麻煩。兩件剛剛好,既留住夏的曲線與隨性,又有秋的微溫與體恤。穿脫之間,仿佛更愛自己一點點。
無端的,這讓我想起北島在《時間的玫瑰》中的一段話:幾乎人人都喜歡狄蘭酒后顯露的溫暖與機智。在他看來,在第三杯到第八杯之間,他是世界上最健談的人,妙語連珠,而三杯之前悶悶不樂,八杯后暴躁不安。
——玄妙之處,一如秋。
四
晨起,抬頭間,見對面楓林間的葵花不見了。秋天,野葵花被砍下頭顱……多少令人傷感、悲戚。
久不在家,花花草草在我的眼中,像時間長河中人的一生,活得大致是個梗概。
除了溫室中水仙等綠植,北方大面積的花事大約要從四五月算起。籠統的北方,時令也不盡相同。一路向北,相同的花期也要拖拖拉拉地差下去。即便南方人眼中“鋼板一塊”的“東北”所屬的遼吉黑,迎春、桃、李等開放的時間,也有微小差別。轉身向南,花季的“時差”就更大了。
比如,今春我從北京回來,玉蘭要敗了,迎春正開,玉淵潭的櫻花想必正熱鬧。家里的各種花草,欣欣然,剛睜開眼睛。仔細觀察,你會發現,今天和昨天,它們的模樣明顯不同。一片嫩芽露頭兒了,是它們在打呵欠;一截枝干伸長了,是它們在伸懶腰。
接下來,它們一股腦地開了,變成爭先恐后的一群瘋孩子。迎春、玉蘭、丁香、桃、李、梨,五月的薔薇,六月的萱草,接下來是瘋得沒邊兒的美人蕉、蜀葵、紫薇、海棠、玫瑰、雛菊、紫茉莉、凌霄、木槿……草瘋長,榆瘋長,都瘋了。
窗外,除草機嗡嗡如蜜蜂。灌木,剛剛剪過平整的短發,清爽了幾分。在亮而高的陽光下,泛著倒影,有往昔的意味和景況,有遼闊的哀愁,如霧彌漫。
閑愁最苦。誠實的勞動可歌可泣。
五
翻出稍厚的被子,睡個扎實的午覺吧。掖嚴被角,仿佛還被愛著。
越來越喜歡棉:棉襯衫、棉襪、棉裙、棉桌布……貼心,體己,托底,妥當,不刺眼,不世故。不管走到多遠,它一直跟從你。像聽話的女兒,像媽媽的飯菜,那感覺,閉著眼睛不會錯認。
午睡剛醒,太陽的日影柔和許多。斜長的影子,也清瘦了。
此時的天光正好,適合畫靜物、水果或人物;也適合水墨,刪繁就簡。或者,讀幾頁哲學書,再望望窗外,聽細颯的清風穿過蔥蘢林木。也許,還可以想想模糊的面孔,用素雅的小楷端正寫下:“見字如面”。思路分外清晰,像吸了過多負氧離子的植物,枝葉清潔端莊。也可能穿戴整齊,去擁擠、豐碩的田野里,拍水稻,聽蛙鳴。
晚霞如炬,像失火的戰車,隆重歡送一日圓滿殞滅。大河遠去,如威猛的雄獅收起吼聲。
采幾支蒲棒、幾束蘆葦、幾個蓮蓬,回家。被我認養,它們便一直活著。倚著書房里黑陶的瓷瓶,繼續做繾綣的夢。
新的轉折,無知無覺,卻又清晰可辨。
(宋曉杰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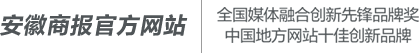
 設為首頁
設為首頁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系我們
聯系我們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