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午落起雨來。
雨也不大。落雨的時候我在陽臺讀一本書的后記,剛讀完雨就停了。陽臺外的香樟樹經雨一潤,綠得發亮。
片刻,雨又斷斷續續地落下。雨聲之外,斑鳩“水咕咕”的鳴叫此起彼伏。
這雨落的是時候。今日谷雨,“清明要明,谷雨要雨”,小時候就聽村里老人這么說。
香樟樹開花了。香樟樹換葉子是清明前后的事,半個月過去,新葉成蔭,碎花如米。
昨夜醒來時聽到鷹鵑的叫聲。去年聽到鷹鵑也是谷雨前夜。鳥雀就是自然的時鐘,每種鳥的鳴叫都有它的時序,既不早到,也不延遲。草木的花期也是如此,每種花的開放也有它的時序,應時而開應時而落,讓人感到安穩。
之所以對這個世界深懷眷戀,就是因為在年復一年平淡無奇的日子里,總有這些自然界細小又美好的事物適時出現,讓惦念從不落空。每次與它們重逢都像是打開生命的序章,而每次的告別又讓我期待著來年的重逢。
夜里鳴叫的鳥很少,鷹鵑算是一種。鷹鵑是杜鵑科,噪鵑也是杜鵑科,噪鵑夜里也會鳴叫。有陣子我分不清它們誰是誰,就把它們統稱為子規,古時候的文人就是這么稱呼的。也有地方把鷹鵑叫做貴貴陽,這是擬音的叫法。以鳥的鳴叫聲來給鳥命名,是人類通常的手段,比如我們村就把斑鳩叫做咕咕鳥。
中午落雨的那刻,聽著遠處斑鳩的鳴叫,心里一動:我臥室窗臺上的“斑鳩之家”現在是什么狀況?幼鳥出殼了沒有?心念一起,就按捺不住好奇心,搬出椅子,站上去,踮腳,隔著陽臺窗戶窺探情況(陽臺與臥室的窗戶相鄰)。啊哈,斑鳩窩里臥著兩只幼鳥,抬頭望著我,毫無懼色。看那情形,估摸著幼鳥已有八九天的鳥齡了。
昨天發現陽臺外的紅葉李樹上也有鳥在筑巢,嘴里銜著長長的芭茅,飛進去,很快又鉆出來。紅葉李的葉子已很茂密,顏色轉成朱紅,一只鳥巢藏在里面,以我的視角看過去,是毫無破綻的。
去年就有鳥在這棵紅葉李樹上筑巢,等我發現鳥巢已是晚秋,樹葉落得差不多了。那只碗狀的鳥巢卡在枝丫中間,整個冬天都在,穩穩當當,下雪的時候,雪堆進鳥巢,高出鳥巢一大截,太陽出來,照得鳥巢閃閃發光,使我生出幻覺,覺得從巢里會飛出銀白色的雪鳥來。
是什么鳥在這樹上筑的巢?并且是在舊巢的位置上,應該還是去年的舊主,或者是去年在這巢里出生的鳥。我是近視眼,就算戴了眼鏡,也不能憑肉眼看出那是什么鳥。那鳥的體型太小了,飛來飛去也是靜悄悄的,不發出聲音,無法從鳴叫聲里辨認。于是拿出相機,等鳥銜著它的巢材飛過來時拍下,看個清楚。
是白腰文鳥。當它再次回到自己的新家(也許是老家),安放好巢材,站在樹枝上小憩的片刻,我拍下了它。想起來了,去年初夏,紅葉李果子成熟時,曾看見一溜文鳥站在果樹最低的枝丫上,大約有五六只,你擠我,我擠你,站立不穩,嘴里發出稚嫩的鳴叫,一看就是才出巢的雛鳥。
每天被鳥鳴喚醒,坐在陽臺上就能聽見從近郊傳來的野鳥之歌,沉浸其間——我知道這并不是每個人都能享受的悠閑。而我能夠在春去春又來的辰光里與鳥為鄰,這就是命運的眷顧,是大自然贈予的最好生活。(項麗敏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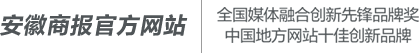
 設為首頁
設為首頁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系我們
聯系我們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