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高眉低看 ·米肖
舊書新讀
海子曾對他的朋友言:成都那個(gè)地方終年陰沉沉,他們那里的人像是在搞什么陰謀。
實(shí)則,寫作何嘗不是在搞一場文字陰謀。倒覺得鐘鳴當(dāng)仁不讓為成都最大的陰謀家。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,說鐘鳴是妖怪。而妖怪相比陰謀家,似少了一口熱氣。
1995年出版的“象罔”叢書之一的《畜界 人界》,在相隔二十余年后的早春夜晚,正被一個(gè)文本愛好者時(shí)斷時(shí)續(xù)翻來折去。燈光于紙頁更迭間,顯得異乎尋常的溫潤,隨之而起的是對廣博文本的驚嘆以及對制造文本主人的敬畏。所有閱讀的夜晚均洋溢著古典主義的陰謀之情———文本制造者與文本閱讀者的良性互動(dòng),靜止于璀璨的一瞬,一條大河逶迤向海,一場盛宴頻臨尾聲,傳花曲終,人飲散盡,剩下的情緒我們姑且將其稱作繁華。
閱讀文本,如入綢莊。上好的緞子慢慢鋪展,綢莊老板鐘鳴端坐于高腳凳上,慷慨于華麗的一一展露,她們分別來自古羅馬、埃及,甚至還帶有“荷馬史詩”的遠(yuǎn)古之風(fēng)。更多的綢緞來自于《山海經(jīng)》《博物志》《搜神記》《古謠諺》《楚辭》《論衡》《爾雅》等。所謂象罔,意即看得見和看不見的。成都綢莊店家掌柜的鐘鳴,以奇異的想象力、廣博的才華把那些隱藏于時(shí)光深處的物事通過文本一點(diǎn)點(diǎn)披露出來。一種蒙茸蒼翠歲寒不凋的觸類旁通,一種通曉馳騁并駕馭中外古今的書寫能力。
蝴蝶、老鼠、狐貍、烏鴉等魚鳥蟲獸在鐘鳴筆下?lián)碛兄鴱V闊的審美意義與凜凜之清氣。對一只老鼠的審美,通過加謬與斯坦貝克的小說路徑慢慢抵達(dá)。你會想象到這樣的文學(xué)敘事該是何等奢華。
一本詭異、古怪、博學(xué)、智慧的書———廣博的才華停駐于樹梢之上的投影。有一種才華,豹子一樣迅捷,轉(zhuǎn)瞬即逝,消耗,幽暗,擺脫,攀花詠月。也似一場大火,幽妙,酷熱,置身于萬壑松風(fēng)之中,漸行漸遠(yuǎn)漸無影。
許多才華漸趨被俗世糾纏辱沒,我們對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物事,皆抱有熟視無睹的木然惘然。惟有鐘鳴在腐朽的糞堆上育出靈芝,在失聲黯啞的世界囈語不絕……
“人畏懼什么,便把什么看作是活物:靈魂,上帝,魔鬼,星星,太陽,影子,燈花,石頭……”鐘鳴筆下書寫的,均是一些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活物。一只鼠到了鐘鳴筆下,讓我們不禁產(chǎn)生了畏懼之情。其實(shí),我們真正畏懼的是———文字。文字才是才華的投影。才華也是一種活物,征服她所要征服的,畏懼她所要畏懼的。
日本文學(xué)講究的是一種“物哀”精神,是垂注,是憐憫,是珍惜,清少納言《枕草子》便是最好代表。而作為詩人的鐘鳴,明顯有著“根深蒂固的南方化的靦腆和冒險(xiǎn)精神”。正因?yàn)橛辛诉@“冒險(xiǎn)精神”,才有了一種將畜界、人界匪夷所思的融會貫通。用詩人王寅的話講,這更是超常持久的熱情和哀傷。但,誰能說哀傷不是源于更深層意義上的另一種熱愛?
書寫,便是不斷地還原靠近內(nèi)心最為隱秘部分的過程。鐘鳴的速度是令人暈眩的,無論狂喜、哀傷,一律是斑斕的。使得閱讀長久地為斑斕所傷,有了無以言說的疲倦怔忳。作家的耐性同樣驚人,簡直是拿虛無來咀嚼,拿宿弊來消化,有盛極而衰的奇崛峭險(xiǎn)。
鐘鳴在自序里坦露,有一些昂貴的書籍是在何多苓和翟永明的資助下才買回來的。到這里,兀自有了辛酸。一個(gè)心遠(yuǎn)的人總是比常人活得艱辛些。這亦是造化,心在高處,不囿于俗世。這亦是一種體面,常人不及的體面。
綢緞莊的門輕輕被掩上。文字的奇險(xiǎn)紛繁而下,間或有黑白插畫點(diǎn)綴。那些插圖,一望而知,便是出自比亞茲萊筆下。鐘鳴詭怪的文字最是要同樣詭怪的比亞茲萊的畫來配的。他倆的風(fēng)格殊途同歸:只要稍稍往前一步,便是壁立千仞的萬丈深淵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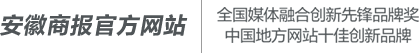
 設(shè)為首頁
設(shè)為首頁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(lián)系我們
聯(lián)系我們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