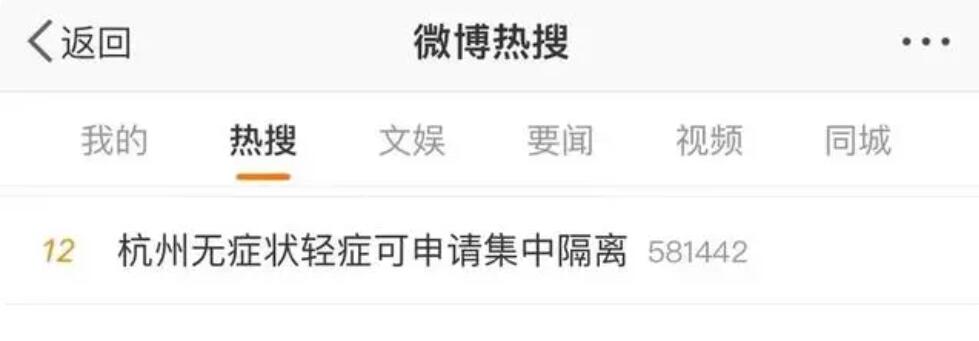一座不斷生長的城(我與一座城)
程 華
霧都、橋都、山水之城……重慶,我生于斯長于斯的家鄉,它的魅力難以盡述。其中最令我驚嘆的,是它不斷生長的姿態。
2023年第一天,我特地從居住的渝北區驅車十幾公里來到渝中區兩路口。行過綠樹成蔭的生態體育公園,邁進暌違多年的大田灣體育場時,我的兩眼瞬間有些濕潤——巨大的橢圓形建筑里,那些充滿中國元素的碉樓、紅墻依然挺立;對面高高的堡坎上,“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”大字依然遒勁……全新升級的紅色塑膠跑道上,是矯健的跑者;綠茵場上,孩子們在歡快地奔跑;還有不少與我一樣,前來體育場懷舊兼“打卡”的市民們……這一切,賦予了這座飽經滄桑的山城地標建筑,以深邃又溫情的意味。
時光回溯到1951年。十三萬山城兒女開赴大田灣開始了熱火朝天的義務勞動。1956年,占地十二萬平方米、可容納四萬多名觀眾的大田灣體育場建成。大田灣體育場先后舉辦過數百次大型體育賽事、大型演出集會、中小學校運會等,這些活動成為重慶人永遠的記憶。上世紀90年代后期,有七八年時間,我經常與同事們來大田灣體育場執行勤務。那時,這里頻頻舉辦球賽與演唱會。我們在忙碌中見證了賽場上那些熱血的時刻,我們一次次在疏導人潮安全退去后,抬頭望見星星綴滿寧靜的夜空……
進入新世紀以后,大田灣體育場漸漸隱退,只有殘破的看臺、陳舊的跑道、瘋長的雜草,述說著這里曾經的榮光。這令無數重慶人唏噓。幾年前,大田灣體育場實施整體保護、修繕和提升的消息傳來,不少重慶人得知消息后,既歡欣又擔憂:大田灣體育場會在整修中變了模樣嗎?如果變了,我們到哪里再去尋找那些珍貴的記憶?
就在大田灣體育場重新向市民開放之際,我迫不及待趕來了。許多重慶人都趕來了。在“修舊如舊”基礎上實現了硬件跨越式升級的大田灣體育場,給了所有人一個驚喜,那是一種久別重逢的欣慰——我們的大田灣體育場回來了!走過近七十年風雨的它,如今以全民健身中心與生態體育文化公園的新姿回歸。當新年的陽光灑在綠茵場上,灑在老老少少活力滿滿的身影上時,整個大田灣體育場煥發出新時代的勃勃生機。大田灣體育場沒有消失,它在新的時代里拔節生長,它的傳奇仍在繼續。
這座城市里,不斷生長的又何止是大田灣?
在大田灣體育場漸漸淡出公眾視野的那些年,我的工作地點從渝中區臨江門遷至幾百米外的滄白路。滄白路距離解放碑不遠,然而,與解放碑的繁華不同,這里路面狹窄、陋巷逼仄。站在十二層辦公樓上,窗外可見煙波浩渺的嘉陵江,俯瞰即是滄白路上的洪崖洞。有著兩千三百多年歷史、地勢起落高差達七十多米的洪崖洞,如同懸于斷崖上的建筑群落,層層疊疊的“吊腳樓”疊出了重慶傳統民居的獨特風情。
直到有一天,我和同事們驚訝地發現,洪崖洞的冷寂被許多頭戴安全帽的建設者打破了。腳手架從崖壁上“嚓嚓”長高,直插云天。新落成的洪崖洞終于揭開“蓋頭”。眼看著游客紛紛涌向這里,我們也坐不住了。下樓,過馬路,走幾步,雙腳就踩在了洪崖洞的頂層——十一層觀景臺。飽覽江上風光后,乘觀光梯下行至一樓。馬路對面,大江湯湯流遠……
依山就勢,沿江而建。飛檐斗壁,紅漆門窗,青磚石瓦。從十一樓到一樓,吊腳樓仍是熟悉的穿斗式結構,但木條變條石,竹墻變磚壁,墻面與支柱注入鋼筋水泥。每至夜晚,渝中半島高樓鱗次櫛比、燈火閃爍,洪崖洞流光溢彩似天上宮闕,吊腳樓高低錯落熠熠生輝。新生的洪崖洞,將巴渝傳統文化與現代時尚風情集于一身。人們驚嘆,古老的洪崖洞不但原地復活,且茁壯生長,長得如此明麗、多彩!
如大田灣體育場、洪崖洞這樣的驚喜,在重慶真是到處可見。一個冬日下午,我踏上位于南岸區的廣陽島。我為這沙洲島上濃郁的春意所陶醉。
有“長江上游第一大島”美譽的廣陽島,其靠山臨水起伏多變的地貌濃縮了重慶山水格局之精華,既有扼守長江要沖的險要位置,又有原生態的自然風光。然而,這個動植物資源豐富的江心綠島歷經興盛與沉寂。最深的創痛當數數年前一場大開發,挖掘機野蠻開進,大貨車恣意飛馳,隨之而來的是山體裸露、土壤沙化……好在,最終醒悟過來的人們按下了終止鍵,飽受創傷的廣陽島終于得以回歸自然休養生息。通過持續精心護山、理水、營林、疏田、清湖、豐草,廣陽島上,白鷺回來了,野鴨回來了,又見綠樹成蔭,蝶飛蜂舞。廣陽島的蝶變,成為重慶“共抓大保護、不搞大開發”的典型案例。
我的家鄉重慶,大山大水在生長,草木林田在生長,亭臺樓榭在生長,夢想與希望在生長。
重慶,一座不斷生長的城。


 設為首頁
設為首頁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系我們
聯系我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