吃點湖鮮
□楊靜
雖已初冬,但氣候依然暖洋洋的,風緩緩的,到處都還是一片秋天的況味。
每日餐桌上,無需多動腦筋,那些豐登的五谷,還有飽食了秋蟲的雞呀鴨呀,都美味得很。牛羊肉暫時不敢多吃,畢竟“秋燥”還在。此時節,水里的魚蝦蟹也正值豐收,且格外飽滿,或許是得益于水之清涼,吃起來也清爽,正適合解解“秋燥”。
有人吆喝要去吃“湖鮮”。這日天氣晴好,大家便直奔女山湖而去。
說到女山湖,多數人乍一聽,可能覺得耳生。其實這湖還是赫赫有名的,從面積上來說,它在安徽是僅次于巢湖的第二大淡水湖;從水系上來說,它曲折蜿蜒,像飛舞著的綠絲帶,從安徽明光境內一直向東至江蘇盱眙匯入滔滔淮河。作為淮河流域的一大湖泊,天生水草豐美,淤泥深厚,歷來是魚蝦蟹安居的好地方。
此湖得名于“女山”,這山也很不一般。這座海拔僅百米的小山,若從空中俯看,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火山口之一。山上草木蔥蘢,湖就在山邊,山湖相連,大大小小的火山石從山坡上一直堆疊到水中,還有不知名的泉水從地下汩汩冒出來,徑直淌到湖里去。
或許湖水得益于這種特殊的火山地質,生長在其中的魚蝦蟹類,味道非同一般,分外鮮甜。
當地人稱之為“女山湖十二鮮”,名列第一的當屬螃蟹。
在螃蟹上桌前,率先登場的必然是一眾魚蝦。只看那一盤盤、一盆盆端上來,清蒸鱖魚片、紅燒淮白魚、黑魚兩吃、角魚燉粉皮、清燉魚頭湯、嘉祐魚丸、氽湯魚餃、辣炒毛刀魚、鹽水青蝦……道道鮮香異常,魚肉滋味鮮甜,口感柔韌細嫩,與平常在市場里購回的各種魚類相比,滋味迥然不同。
最讓人不忍停筷的是“淮白魚”。其實白魚并非淮河水系的女山湖獨有,巢湖里有,太湖里也有,著名的“太湖三白”,白魚就占了一席之地,本不稀奇。然若論起品質、名氣及歷史,別地白魚則無一能與淮河白魚相比肩。有史可查的是在夏禹時代就有“淮夷貢魚”記載,這魚指的就是白魚。歷唐而宋,“淮白魚”名氣越來越大,江淮白魚用桶裝遞運京師,已成定例。
白魚適合清蒸,而今我們面前的這桌湖鮮,清蒸的位置讓給鱖魚了,白魚只得紅燒。這是一條約兩三斤重的白魚,廚師將其從中斬為兩段,用湯汁紅燒,聞起來鮮香馥郁,魚肉雪白細嫩,入口綿軟,且有一股特別的香甜氣息。
清蒸野生鱖魚也是絕美。鱖魚切片,大火快蒸,盤中只需淋入少許生抽,那種純純的鮮甜感,好吃到咬舌頭。
當地人家自制的魚丸、魚餅也是極好,人稱“嘉祐魚丸”。嘉祐是宋仁宗年號,可見在900多年前,此地魚丸也是頗有名氣了。
桌上除了魚蝦,僅有的素菜也是湖鮮,清炒菱角米,素拌菱菜梗。若運氣好時,還能碰上雞頭梗(芡實梗)。當地老饕建議,其它蔬菜最好別點,因為點了也少有人吃。
魚蝦下肚,螃蟹壓軸登場,紅彤彤的“鐵甲將軍”盛在大盤里。還未到桌前,一股鮮味已將鼻腔徹底阻塞,再也容不進其它味道。捋起衣袖,伸手抓起一匹大個的。眾人默不作聲,只細細吃將起來,一匹匹鐵甲將軍轉眼化為腹中之物。
和別處相比,女山湖的蟹成熟期偏晚,每年11月至12月間最佳,正適合這個時節品嘗。此蟹實在是妙呀!殼青肚白,干凈鮮美,蟹黃色澤紅澄澄的,顆粒飽滿厚實,似有溢出蟹殼之勢;蟹肉白嫩細膩,入口綿中有韌,和這湖里的魚蝦一樣,別有一股甜絲絲的味道,完全不需要蘸醋,吃的就是最本真的原味。
吃罷湖鮮,大家沿著山,去了湖邊一處叫做蝴蝶谷的地方。據考證,金庸先生在《倚天屠龍記》中描寫此處:“常遇春知道胡師伯不喜旁人得知他隱居所在,待行到離女山湖畔的蝴蝶谷尚有二十余里地,便打發大車回去,將張無忌負在背上,大踏步而行……其時已是深秋,但蝴蝶谷一帶地氣溫暖,遍山遍野都是鮮花……”當地人介紹說,此處“地氣溫暖”,正是這里特有的火山地貌具備的條件。
我們沿著湖堤漫步,深秋氣候,堤邊還真有鮮花盛開,恰巧有蝴蝶不知從哪兒飛來,落在花芯上,輕輕揮舞著翅膀。夕陽斜照,波光粼粼,這蝴蝶谷安靜而美好。
地栗何足數
□呂峰
“晚菘細切肥牛肚,新筍初嘗嫩馬蹄。”荸薺又名馬蹄、地栗,最早見于《爾雅》:“芍,鳧茈。”每一個名字都字如其物,其發音皆有一種清脆的感覺,嘴邊似有脆生生、甜潤潤的汁液。剛采下的荸薺,色澤鮮艷,潤潤水靈,甜美無比。
荸薺多植于池沼、水田,幾場霜雪過后,即可收獲。李時珍對荸薺的介紹甚為詳細:生淺水田中。其苗三、四月出土,一莖直上,無枝葉,狀如龍須……其根白蒻,秋后結顆,大如山楂、栗子,而臍有聚毛,累累下生入泥底。
荸薺可直接生食,去皮后,果肉白凈如玉。入嘴,汁液甘冽,清脆爽口,那種脆嫩的質感,讓人著迷。荸薺自古即有“地下雪梨”之美譽,有著誘人的甘香與鮮美。對許多人來說,荸薺就是一種饞嘴的水果,也是頗受喜愛的時令之物。
荸薺入饌,滋味極妙。水煮尤能得其真味,將之洗凈放入鍋中,加水燒開后,用文火煮上二十分鐘,直至心透明即可。煮好的荸薺,甘甜脆韌,連煮荸薺的水也甘甜無比。在寒冷的天氣里,吃上一碗水煮荸薺,再喝下一碗溫潤的荸薺水,整個身心都暖和起來。
荸薺可單烹,亦可與其它食材搭配,如荸薺蝦仁、荸薺雞丁、荸薺肉片等。荸薺直接入饌,可為菜肴增加脆爽的口感。如荸薺肉丁:將其切片,佐以青椒與肉片同炒,肉的滑嫩與荸薺的爽脆格外搭配。看著那一盤美色,感覺能多吃一碗飯。哪怕是席間油膩吃多了,吃上兩口荸薺,頓覺口中清爽,胃口又起。
荸薺亦可做成糕點,廣州有以荸薺粉拌合糖水蒸制而成的馬蹄糕,極為有名。正宗的馬蹄糕,呈半透明狀,茶黃色,可折而不裂,撅而不斷。北京有玫瑰荸薺糕,將荸薺剁成泥,摻上面粉拌勻,團成球形,入油鍋炸。再將白糖、玫瑰花熬制成汁,澆至荸薺球上。吃起來,細膩嫩軟,滋味香甜,有馥郁的玫瑰芳香。
荸薺、山楂、梨一起燉煮,是冬天里最溫暖的甜湯,紅紅白白,看著即讓人心生歡喜。對荸薺,我甚為喜愛。每次遇到鮮荸薺,都要購買些,只需在水里洗一下即可。吃時,不用刀,直接用牙啃皮,那“沙沙”的聲響,悅耳動聽,吃進嘴里則是讓人沉醉的甘甜。
有一次去蘇州,街頭巷尾有鮮荸薺售賣。一顆顆躺在竹筐里,如江南老式家具的古拙之色,散發著動人的光芒,讓我收獲了意外之喜。一邊走在古色古香的街道上,一邊不顧形象地啃食荸薺,引人注目。當地朋友大笑不已,見我如此喜愛荸薺,遂對我講起了荸薺在蘇州的故事。
舊時,在江南水鄉的沼澤、水塘里,生長著許多野荸薺。農閑時,男男女女會去采摘荸薺,江南話是“斂荸薺”。說是采摘荸薺,其實是借此機會相會。朋友說到興起之處,情不自禁地唱起彼時的情歌:“姐在田里斂荸薺,斂著一個大荸薺。汏脫爛泥剝脫皮,輕輕塞到郎嘴里。問倷郎啊啥滋味,賽過山東甜水梨。”鄭逸梅說其介于果蔬之間,啖之味清而雋,有如讀韋蘇州之詩。如今讀其文章,頗為有趣,像荸薺的味道,有清新可人、自然天真的甜脆。
如果說鮮荸薺是妙齡少女,風干的荸薺則是耄耋老人,如老樹虬干,堅硬無比。風干的荸薺不耐看,卻中吃,吃起來甜味濃濃,別有風味。蕭紅在回憶魯迅先生時,特意提到了風干荸薺:風干荸薺就盛在鐵絲籠,扯著的那鐵絲幾乎被壓斷了在彎彎著。一推開藏書室的窗子,窗子外邊還掛著一筐風干荸薺。
汪曾祺在《受戒》中描述小英子崴荸薺的情形:“赤了腳,在涼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著,——哎,一個硬疙瘩!伸手下去,一個紅紫紅紫的荸薺。”古時,荸薺是嘗鮮解饞之物,亦是救命之食。明人王鴻漸在《野荸薺圖》中稱:“造物有意防民饑,年末水患絕五谷,爾獨結實何累累。”稻谷受災,荸薺卻能結實累累,供人充饑,堪稱是造物之妙。
北風日緊,最適宜吃清甜滋潤的荸薺。正如周作人所言,荸薺是“有格”的果蔬。
豐腴清淡之間
□錢紅麗
同事自女山湖帶回螃蟹、魚丸,慷慨贈我。她回來已近晚八點,雖說早已吃過晚餐,但一刻也等不及,連夜蒸了螃蟹,鮮香馥郁。母蟹豐腴,膏黃遍布整個腹胛,掰開,黃油淌了一手。公蟹的膏,細潤如白玉,大螯、長腿肌肉飽滿而有張力,別有韌勁。小孩子一開始不太感興趣,待品嘗到一條腿肉后,根本停不下來。腿肉盡剝,悉數喂他。他一邊吃一邊感動,道出無數“謝謝”。
中秋前后,蟹正蛻變,沒有吃頭,黃呈流質,尚有苦意。吃蟹,初冬正是時候。
小孩居校,伙食寡淡,可憐得很。正計劃做一小瓶禿黃油,等他回來,拌面,抑或炒飯。也還想做一道蟹粉獅子頭。
這邊菜市的蟹,多來自固城湖、沱湖,雖不及女山湖的肥美,畢竟季節到了,滋味應不太差。
有一年,也是初冬,忽啟宏愿,剝出兩只蟹粉,靜等小孩放學享用,花去整整一小時。太過專注,一直埋首低頭,等蟹剝完,犯了頸椎病,整個人目眩神迷,僵硬得直不起腰。自此發誓,往后再也不做二十四孝媽媽。
迫于頸椎病的威壓,一直延宕著未去菜市買蟹,直至終日行臥不安,總歸心里有一樁事未完。
嗯,就在這幾日,一定要實施起來。
一小瓶禿黃油,至少需要十只肥蟹吧。洗凈,一只只碼在籠屜,蟹肚朝上,以便黃油淌掉,隔水干蒸二十分鐘。剝一只,取一只,余下的,鍋中保溫。涼了,肌肉收縮,更不易剝。依靠蟹八件,大約需要花費四五小時吧。
蟹粉剝好,熱鍋化開豬油,下姜絲煸香,匯入蟹粉,熗炒一兩分鐘,倘有雞湯更好,澆一瓢進去(大骨湯替代亦可),改文火熬煮四五分鐘,大火收汁。涼透,裝入玻璃瓶中,再倒入化開的豬油,淹沒蟹粉為宜,起隔絕空氣之用。吃一年,也不變質。
等小孩回來,可以先做一道蟹粉獅子頭。豬前胛斤余,肥瘦四六開,切成石榴籽粒大小備用。老姜切細絲、小蔥一把,浸于涼開水中二十分鐘,潷出姜汁水,待用。豬肉粒放入大瓷盆中,適量鹽、淀粉,三四勺禿黃油拌入,同一方向攪拌、摔打,令其上漿,一邊摔打,一邊兌點姜汁水進去,去腥增香。差不多摔打十分鐘,團起一只只肉丸,隔水干蒸十分鐘。砂鍋內適量雞湯,鍋底墊一層黃芽白葉子,獅子頭輕輕放入,上面再覆一片黃芽白葉子,蓋緊鍋蓋。大火頂開雞湯,改文火咕嚕,大約半小時吧。
淮揚版獅子頭里放荸薺。大可不必,蒸煮齊下,肉一定不會柴,口感想必粉嫩。吃獅子頭,要輕輕舀進碗中,用湯勺一點一點搲著享用。
有一年深秋,與孩子同看美食類紀錄片,上海有一家專營禿黃油炒飯的店鋪,主顧們皆為白領。店主舍得放蟹粉,一盤炒飯里,遍布橘黃蟹膏,定價不菲:180元一份。彼時,看得唾液橫飛,當時承諾,等哪天我們去滬上,也叫上兩份。
何不自己動手呢?倘有一罐禿黃油在手,便好辦。適量嫩豌豆、胡蘿卜丁豬油焙熟,再打兩只雞蛋,匯入米飯,炒至米粒在鍋中跳舞時,加入禿黃油,熗炒一分鐘,讓每一粒米飯上都裹滿禿黃油,撒一撮香蔥,起鍋裝盤。
還有另一道美食——蟹粉匯黃菜。黃菜,即炒雞蛋,想必美味。
河蟹應是這個星球上第一等鮮物,海蟹無論如何是比不上的。河蟹體內蛋白質釋放的鮮,是最高級別的鮮,魚蝦雞鴨,鵝豬牛羊根本不可追。母蟹之黃,公蟹之膏,其口感,無一可比擬,滋味殊異,年年相似,又年年境界不同。
每年啖螃蟹,結束時,總是悵然若失,雙手洗了一遍又一遍,明明不餓,因為一點一點地啜,耗時費力,到末了,還總將自己吃餓了,一味后悔懊惱——也沒吃到什么,蟹螯碎刺還將嘴唇劃破。早知如此,不如不吃。可是,翌年,照樣就范,總要饕餮一回——不如此,生命仿佛缺了儀式感……一年年的,悔意是真的,饞意洶涌也是真的。
然而,人生里大多餐食,均由蘿卜白菜組成。一日日吃起來,最得燈火可親余味。
居所附近有一大型商業用地,幾十公頃面積,荒廢很久很久,陸續被老人們用來墾荒了。時入初冬,青菜蘿卜被清霜浸染幾夜,最得鮮美滋味。
近日,正大量上市。要起得早些,才不會錯過這珍貴蔬菜。
有時,午餐,只一樣蘿卜。頭天煨了一罐肉。蘿卜切滾刀塊,鍋里稍微一點素油,將蘿卜辣腥氣熗炒掉,添幾勺鹵肉湯進去,一忽兒烀爛,再撕幾快肥瘦相間的鹵肉,爆炒幾下,起鍋。
一餐,最多米飯半盞。情不自禁,將蘿卜湯一并傾倒飯中,嘩嘩嘩,不及兩分鐘,所有米粒皆入了胃囊。
我好像沒有細細咀嚼?是太美味了,還是米粒被湯汁浸泡變得滑膩,來不及咀嚼?兩者皆有吧。
羊肉給冬天供暖
□張言
冬天不會獨自到來,總有一種食物搶先喚醒季節味覺,比節氣還準。
寒冷清晨,胃里有顆種子突突震顫,急待一碗熱氣騰騰的羊肉湯澆灌。一刻也不想等,飛奔去老楊湯鍋。
熬了二十年的老湯白浪翻滾,熟爛羊肉鍋中浮沉,水氣繚繞如冬霧,老楊偏頭避開水霧,熟練叉起羊肉,趁熱切塊,與羊頭、羊肚、羊雜組合成不同內容的湯。
膻是一只羊凝固在血肉里的鮮,火焰化開膻鮮融進湯汁,腴白老湯翻滾出純粹肉香,微黏汁液飽含養分,搭配緊實筋道的高莊蒸饃,雪湯白饃,虛實相間,猶如一首平仄得當韻律優美的宋詞。小楊一個托盤端四碗湯,挨個唱念“二十嘞羊肉羊頭”“三十嘞羊雜羊腰”……是誰的,誰舉手應一聲,小楊飛快地走到面前,放下碗走人,滴湯不灑。
兩行楊樹綿延數十公里,樹與樹之間系棉繩,鮮紅芋秧子搭在繩上曬,那是養羊人給羊準備的過冬草料。鮮芋秧汁液甜稠,老羊在一堆綠色里,用舌尖挑出芋秧細細咀嚼。繩上鮮芋秧逐漸失去水分,綠變黃轉成黑褐,與剛剛做成的白粉絲掛在同一行樹上晾曬,一棵紅芋的前世今生,黑白分明。
沒人把羊當動物看,冬天里更是。活羊是行走的食材,不時有人去養羊戶家中挑羊詢價。黑黃兩只土狗,與羊活在一起,臥在玉米秸稈上,盡心盡責守護羊群,見人過來警惕地低吠。它倆還不知道,這個冬天過后,二十多只羊,只會剩下寥寥幾只。
羊吃了干草,去掉青草氣,肉質肥潤細膩,更加契合逐暖的胃。羊肉性熱滋補驅寒,多食卻令人上火,唯冬土長出的蘿卜能平和肉里燥氣。經霜紅蘿卜白瓤水脆,寒冷凝結糖分消解許多辛辣,削皮取瓤與羊骨燉至軟爛透明,微抿即化,如肉似髓,滑糯到可吸食。
小菜園種的紫色冰激凌蘿卜,萬萬舍不得煮吃。小紫蘿卜最多長至嬰兒拳頭大小,表皮光滑紫靈,無渣無須,連皮一起吃,分外甜嫩。笑臉蘿卜更小更幼,紅白配色,上紅下白,笑臉般可愛。“笑臉”只長到一元硬幣大小,玲瓏如珠,肉質柔糯,一口一個。
初冬陽光明亮如春,田地里油菜苗綠意盈盈。油菜籽小米般大小,種時不免多播,出苗驚覺過于稠密,離一拃一棵的間距,多出數倍。一行一行種,出苗后一棵一棵剔,比種時還費勁,蹲得腿疼。剔出的油菜嫩苗,脆而無絲,蒜瓣熗鍋爆炒,不待出汁盛出,自帶油菜咸鮮,無需多加鹽粒。
勤儉的鄉下老太,看不得好好的菜苗擱焉,牙口不好的她們,將油菜苗切成短段清炒,與老豆腐一起煮至酥爛,既補充了維生素,又補充了蛋白質。
大棵油菜苗去根,投入熱水鍋中略燙,攥干水分,攤在高粱蓜子上曬干,留著冬天煨肉包包子。捋掉的青葉也不浪費,鄰居家養了三只鴕鳥,還未長到嬎蛋年歲,正貪吃青葉,他去地里拾拾撿撿,滿滿一筐背回去,能省下三棵白菜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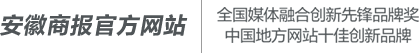
 設為首頁
設為首頁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系我們
聯系我們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