東北的“冬”
◎楊靜

第一次去東北,正是隆冬。20多年前的一個(gè)春節(jié),南方“小土豆”把自己里三層外三層包裹起來(lái),踏上了前往東北的旅途。
首站是長(zhǎng)春,沒有直達(dá)專列,需從蚌埠或北京中轉(zhuǎn)。火車很慢,空間交錯(cuò),驟然壓縮,兩天一夜都在車上,相鄰鋪位的旅客熱烈閑談,下車時(shí),幾乎處得像老朋友一樣。
一路北上,滿目濃綠漸成千里冰封。從零上8度的地方,來(lái)到零下28度的北境,下車那一刻,冷涼徹骨的空氣將人包圍,感覺不是“冷”,是“透”,寒氣仿佛x光,瞬間把人從外到里照了個(gè)遍。好像夏天做涼面,將面條從熱鍋里撈出來(lái),再放在涼水里一湃。對(duì),就是“湃”,南方“小土豆”被東北的凜冽冰鎮(zhèn)了。
所幸很快又上車,待到進(jìn)入室內(nèi),抖落全身衣物,則又暖和得像夏天一樣。朋友是長(zhǎng)春土著,住在紅旗街上,屋里地暖燒到最熱,穿短袖,光腳,啃一塊老冰棒或是糖葫蘆,再啜一個(gè)凍梨,窗外雪花飄飄,只有“愜意”兩個(gè)字可以形容。
貓冬生活,溫暖而幸福。也出門玩,把自己從頭到腳包裹到位,在運(yùn)動(dòng)中并不感覺太冷。坐54路有軌電車,去南湖公園,湖水凍透了,全部結(jié)成冰,在湖面上溜冰梯、滑爬犁,還有騎馬、開小汽車之類的項(xiàng)目,大人孩子你追我趕中,都是熱力發(fā)動(dòng)機(jī)。
都說(shuō)南方是“凍人不凍物”,北方則是“凍物不凍人”,經(jīng)歷了才真正體會(huì)到。初次的東北行還收獲了“意外”禮物,之前大概從中學(xué)起手腳生凍瘡。“一年凍,年年發(fā)”,每至冬季,滿手凍瘡苦不堪言,不能根治。那次東北的極寒之旅,帶著一手凍瘡去的,不知是因?yàn)楸桓涞目諝狻芭取绷说脑?還是被室內(nèi)的溫暖治愈,回到合肥,凍瘡全部消失,再未復(fù)發(fā)過(guò)。
次年再去東北選擇了國(guó)慶假期,打算看看“北方之秋”。真實(shí)感受,還是經(jīng)歷了一次“冬”。
那次跟著東北一個(gè)戶外俱樂部去爬黑龍江的兩座山。第一座是五花鳳凰山,山腰下展現(xiàn)的正是濃烈的秋,楓葉紅得鮮艷,落葉松金黃奪目,魚鱗松、樟子松不動(dòng)聲色,仍是偉岸的綠。楓的鮮紅,落葉松的金黃,樟子松的綠,加上高高的白樺,豐富色彩繪成巨幅畫卷,美麗極了。
等爬到山頂,卻遭遇了一場(chǎng)初雪,白樺林披著白雪,形面璀璨的樹掛,陽(yáng)光穿破烏云在遠(yuǎn)處的群山之巔橫成玉帶,陽(yáng)光漫漫灑下,遠(yuǎn)山間的五花畫卷隱約可見,身旁卻是伸手可觸的冰雪。秋冬交替,出現(xiàn)在同一空間,宛如夢(mèng)境。
跟著又去登了黑龍江最高峰大禿頂子。那時(shí)的大禿頂子完全沒有開發(fā),原始森林狀態(tài)。有靠譜的人帶隊(duì),荒山野嶺也不怕。正趕上一波冷空氣降臨,山下小雨,接著是雹子,爬到山腰雪花紛飛。把背包里所有能裹上身的衣物全部穿上,還是冷!
當(dāng)晚在山頂扎營(yíng)。一早,費(fèi)力拉開帳篷門,厚厚的雪一下跌落。大雪是飛舞了一夜啊!天地白茫茫一片,上面是白云,下面則是白雪,整個(gè)連成一體,而我們,就如山上的一樹一石一草,自然而然。
后面又坐了6345次普慢,就是現(xiàn)在俗稱的“雪國(guó)列車”,歷時(shí)24小時(shí),穿越大興安嶺,去北極漠河。
才十月初,漠河已是零下10度,供上暖氣了。假期尾聲,沒有什么游人,我們住在北極村里,沿著黑龍江邊散步,江對(duì)岸,是俄羅斯村落,有俄羅斯人騎著摩托出門,不需望遠(yuǎn)鏡,看得清清楚楚。
我們還去拜會(huì)了漠河鄉(xiāng)政府。時(shí)任鄉(xiāng)長(zhǎng)侯振坤剛從俄羅斯考察回來(lái),他滔滔不絕介紹漠河的方方面面,還把各樣規(guī)劃拿出來(lái)給我們看,說(shuō)漠河未來(lái)要建滑雪場(chǎng)、飛機(jī)場(chǎng),洛古河村要建黑龍江源文化碑,胭脂溝要建金礦遺址等等……如今,漠河早已成為南方“小土豆”們心心念念打卡的旅游勝地,那些項(xiàng)目應(yīng)該早就建成了吧。
再想到東北的黑龍江冷水魚、大骨頭燉酸菜、汆白肉血腸、土豆燉大鵝、苞米團(tuán)子、蘸醬菜……唉呀,口水流了一地,必須趕緊再安排一次東北行。
東北記
◎南窗紙冷

東北今年大熱,社交媒體上鋪天蓋地的攻略、視頻、新聞,是想裝看不到都難的地步……東三省我是都去過(guò)了,只是心心念念沒有坐過(guò)一次雪國(guó)列車。今年本想從哈爾濱坐個(gè)臥鋪去漠河,但如今爾濱那么火,決計(jì)還是等一等,稍稍避一避熱度,把機(jī)會(huì)讓給還沒去過(guò)北方的人。
說(shuō)起來(lái),哈爾濱給我的印象還是“好吃”。第一次去哈爾濱時(shí)還沒到三十歲,南方人第一次去那么北的地方,走在路上,忽而就會(huì)飄起鵝毛大雪,那份心里的驚異,大約和如今的“南方小土豆”無(wú)異。大街上吃馬迭爾雪糕,路邊的商店賣著貂,走得累了,鉆進(jìn)一家店吃粉條燉大馬哈魚,太好吃了,十幾年過(guò)去了,此后再也沒吃過(guò)那么美味的魚。馬迭爾雪糕后來(lái)全國(guó)各地都有賣,但我堅(jiān)持認(rèn)為,當(dāng)年吃的味道才是最對(duì)的。
秋林紅腸也是當(dāng)年首次吃到,直到如今,我還喜歡自東北買紅腸。有時(shí)不想做飯,切切一碟子再炒個(gè)青菜,就能送下一碗米飯。米,也是東北大米,感恩黑土地的福澤。
小時(shí)候在北京上學(xué)時(shí),河道結(jié)冰是常事。可到了哈爾濱,松花江結(jié)冰的盛景還是大為震撼了我。冰層很厚,隱隱透出江水的碧色,有著阡陌縱橫的裂紋。我穿著雪地靴,穿過(guò)江面去了太陽(yáng)島,那天足足走了十三公里,竟一點(diǎn)也不覺得累。
后來(lái)陸續(xù)走完了東三省。因著去遼博看大展,接連去了好幾次沈陽(yáng)。我總是住在沈陽(yáng)故宮邊的一個(gè)快捷酒店,地段很好,只要一百多元一晚,還供早餐。曾有一次為著趕時(shí)間,只匆匆忙忙吃了半碗面,餐廳阿姨大著嗓門問(wèn)我,姑娘,你再帶上兩雞蛋,路上吃啊?
去吃老邊餃子。自門外就能見到屋里的熱氣騰騰,我只有一個(gè)人,被領(lǐng)到樓梯下的一個(gè)小獨(dú)座桌兒。我要了盤餃子,炒了盤蘑菇,上來(lái)之后才發(fā)現(xiàn)吃不完,真吃不完。分量太大,在我南方足可供兩人食用。
遼博館藏古書畫是中國(guó)書畫界的半壁江山。我在那里先后看了《虢國(guó)夫人游春圖》《簪花仕女圖》《瑞鶴圖》,后來(lái)還看了吉林博物館借出的《文姬歸漢圖》,大概這也是生在這個(gè)時(shí)代的幸運(yùn)之一,千百年來(lái)最好的東西,竟然能親眼見到。
去長(zhǎng)春時(shí)看偽滿洲國(guó)皇宮博物館,那日極寒,我穿上了全部衣服,還是被穿堂風(fēng)吹得瑟瑟發(fā)抖。長(zhǎng)春的游客不多,有著非常經(jīng)典的東北城市風(fēng)味,日光冷淡,天黑得很早。巨大的煙囪懸在城市上空,不分晝夜噴著白霧,吹遠(yuǎn)去,就成了云。路邊未融化的積雪在朔風(fēng)之下碎成了小小的冰粒,經(jīng)過(guò)的車又將它們卷到了路面上。一陣風(fēng)吹起,好似一層霧籠過(guò)。
哈爾濱的冰雪大世界很火,長(zhǎng)春有冰雪新天地。一樣有冰雕、煙花、娛雪項(xiàng)目。去長(zhǎng)春時(shí)我?guī)Я撕⒆?我們兩個(gè)拖著重重的雪圈,坐在上面,自冰雪坡道上滑下來(lái)。都是新手,我們兩個(gè)伸著四條腿,向下扒拉自己的雪圈,呼的一聲,下去了,一路冰花四濺,甚至?xí)缘阶炖铩D欠葺p盈感后來(lái)曾反復(fù)出現(xiàn)在我的腦海里,大約,也會(huì)滋養(yǎng)小孩的童年記憶吧?
寒風(fēng)吹徹
◎錢紅麗

一位旅行北歐的博主說(shuō):試過(guò)在冰天雪地中等車嗎?那感覺就像在機(jī)場(chǎng)等一艘船。站牌顯示還有8分鐘,這是北歐第一次對(duì)你說(shuō)謊,也不是最后一次。
這一段文字感同身受,寒風(fēng)中的8分鐘,當(dāng)真漫長(zhǎng)如年。不曾體味過(guò)嚴(yán)寒的人,不足以語(yǔ)人生。想得到嗎?一段文字,令我在精神層面寒顫連連。想起那年寒冬在天津高鐵站,不知為何,北方小姐姐那么急迫,竟然提前20分鐘將寥落的幾個(gè)乘客放進(jìn)月臺(tái)枯等。
北方的天空高遠(yuǎn)空闊,青楊樹葉子落得一片不剩,全世界的蕭瑟荒涼,齊齊聚集了來(lái)。佇立月臺(tái)的我被寒風(fēng)圍困住,哀告無(wú)言,瑟瑟發(fā)抖……相鄰的一對(duì)夫婦試圖前來(lái)攀談,我痛苦地?cái)D出笑容以示回應(yīng),再無(wú)熱量接話——怕一張口,冷風(fēng)倒灌,從頭到腳穿心涼。
那是一生中最漫長(zhǎng)的20分鐘。至今憶及,我全身骨頭還是涼的。涼透了,一直暖不過(guò)來(lái)。
天津那座酒店作為舊時(shí)代的國(guó)賓館,頗有些年頭了,莊嚴(yán)灰舊,遍布光陰的質(zhì)感,何談雙層玻璃?洗澡時(shí)熱水器不工作,重新?lián)Q房間,立刻感冒,翌日涕淚橫流。午夜,朔風(fēng)哨子一樣尖叫,偶爾切換為嗚咽之聲,更多時(shí)像極防空警報(bào),讓我深感孤單、驚懼……那種孤立無(wú)援,也像小時(shí)迷了路,一直走不出那座山岡,眼看太陽(yáng)落山,整個(gè)世界都拋棄了我的恐懼啊。
北方何以給我這樣一個(gè)下馬威?這些年,走過(guò)一些地方,偏多溫暖之地。一樁樁一件件回憶起來(lái),遍布琥珀一般的暖色調(diào),俱成美好往事。但北方那種倨傲的冷,一點(diǎn)點(diǎn)逼出個(gè)體生命的不得已。四五年過(guò)去,依舊不能面對(duì)自己泥足于寒冷的軟弱無(wú)能——真是對(duì)我靈魂的極大摧殘,無(wú)力反戈一擊。
那幾年,忽遭工作環(huán)境的暴擊,一口氣尚存,總歸要離開的。可是呢,臨了又被理智勸住了,反復(fù)拉鋸戰(zhàn)般消耗自己,一如那個(gè)朔風(fēng)呼嘯的午夜。
假若三十歲就好了。到底未能挪步的原因,多是我殘山剩水的身體再也不敵風(fēng)寒。后來(lái),每每遇事舉棋不定,便想起天津高鐵站那瑟瑟發(fā)抖的20分鐘,漫長(zhǎng)無(wú)告地望著列車來(lái)臨的方向,凍木掉的兩只腳,來(lái)回切換著輕輕跺在水泥地上,愈焦急,時(shí)間愈顯漫長(zhǎng)……
小時(shí)候的寒冬,也冷。坐在教室,雙腳木然。但小孩子有熱望,下課鈴驟響,便得救了,風(fēng)一樣跑出教室,小伙伴們默契地依墻而立,相互擠暖,體內(nèi)的血液快速流動(dòng),我們的臉龐彤紅,手足俱暖。這珍貴的10分鐘賦予童年深厚底蘊(yùn),一輩子憶及,都是甜的。童年是趨光的,勃發(fā)的生命力天生可以御寒。如今,我生命的燭焰漸委,縱然一息心力尚存,肉身的廬舍難抵風(fēng)寒。
同是寒冬,我又去了石家莊。去酒店,一路均是灰蒼蒼的,天是灰的,整座城是灰的,默默跟了我們一路的太行山,貝葉經(jīng)一樣似壓于箱底幾千年的灰塵撲面,別無(wú)一點(diǎn)生機(jī)。天色向晚,眾人站酒店前,等車間隙,忽地一陣妖風(fēng),眼前一棵小葉榆樹,瞬間卸落一身黃葉,片甲不剩。眼前一幕,令我呆怔,大為驚駭,確切地說(shuō),是破防了。這北方的風(fēng),來(lái)如驚鴻,一如鬼拍掌,何等殘酷,一掌下去,諸葉皆盡。
在我久居江淮的經(jīng)驗(yàn)里,樹葉是一片一片一天一點(diǎn)落掉的,宛如大提琴的沉思慢板,自深秋拉到初冬,一片一片由綠到黃,春花十萬(wàn)如夢(mèng)里……眾葉凋敝,至少要用去兩周時(shí)光。
誰(shuí)曾想,在北方,萬(wàn)物凋敝僅僅數(shù)秒?
坐在酒店隨便一個(gè)角落,均能望見太行山剪影,不得不想起荊軻刺秦的遙遠(yuǎn)舊事。正是在這太行山腳下,燕太子丹易水河畔送荊軻,用文人的語(yǔ)言概括:風(fēng)蕭蕭兮易水寒,壯士一去兮不復(fù)還。這是死別啊。也只有苦寒北地,可以產(chǎn)生這樣的文學(xué)。倘若在溫暖的杭州,唯有折柳作別了,或者《梁祝》纏綿悱惻的“十八相送”。越劇是何等的至柔至糯呢?杭州這樣的南方之城,無(wú)論如何產(chǎn)生不了荊軻這樣的壯士。
壯士注定要為苦寒所鍛造。
詩(shī)人樹才老師說(shuō)過(guò)一段話。大意是,人只有呆在寒冷的北方才能寫出點(diǎn)東西來(lái),要是整日流連于杭州,置身山光水色之中,哪有心思創(chuàng)作呢。
斜風(fēng)細(xì)雨柳綠花紅之地,最能消磨人的心性。高寒國(guó)家如俄羅斯,何以產(chǎn)生那么多杰出天才?無(wú)論文學(xué)界、音樂界、繪畫界,一個(gè)個(gè)均是苦寒中來(lái)的,活出了個(gè)體的尊嚴(yán)。
所居酒店,設(shè)有河北省圖分館,借出幾本好書。一夜夜,枕著風(fēng)聲批閱,不覺夜深——縱然窗外朔風(fēng)呼嘯,到底有書籍作伴,靈魂有所安頓,不再驚懼。
并非虛妄之言,文學(xué)確乎可以用來(lái)防身的——假若什么都失去了,不必害怕,至少還有文學(xué)這根定海神針呢。
之后,離開石家莊,去了正定,拜訪隆興寺,見了那尊翹著二郎腿的觀世音。菩薩那么美,晦暗的寺里,佇立久之,默默許了一個(gè)愿。
今天凌晨,看見一個(gè)博主錄了自己孩子的一個(gè)小視頻。一歲多的孩子看見陽(yáng)光灑在沙發(fā)上,高興壞了,用小小的手去捉……底下幾百條留言,一樣講到自家孩子種種天真之事。我津津有味讀下去,真是一個(gè)美好早晨,縱然窗外中度霧霾的天氣,也不必介意。
這是什么呢?這不就是向苦而生嗎?我們要時(shí)刻像幼童那樣,不失一顆赤子心,懂得每一縷陽(yáng)光的珍貴,開心地向每一日致敬。雖然冷冽酷寒,還是向往北方,東北、內(nèi)蒙、新疆,一直是夢(mèng)寐之地,總有一天抵達(dá)。
那年寒冬的清晨,我自正定離開時(shí),天降大雪,華北平原一夜白頭,叫人始終不能忘記。
爾濱二三事
◎風(fēng)舉荷

吳伯凡有次做節(jié)目,說(shuō)自己大學(xué)畢業(yè)時(shí),有個(gè)同學(xué)考上美國(guó)研究生,回家向老父征詢意見,老爺子沉吟半晌:“你去也行,我們就當(dāng)你死了。”吳伯凡1987年畢業(yè)于中國(guó)人民大學(xué),在上世紀(jì)80年代人的心中,美國(guó)確如天邊一樣遙遠(yuǎn)。
我爹是文革后第一屆高考生,我問(wèn)他,為什么當(dāng)年會(huì)報(bào)考合肥工業(yè)大學(xué)?他漫不經(jīng)心說(shuō),因?yàn)槟鞘俏覡敔斂坎叫幸惶煲灰咕湍茏叩降膶W(xué)校。當(dāng)年以他的高考分?jǐn)?shù),上清華也沒什么問(wèn)題,但農(nóng)民的兒子一心想考“工業(yè)大學(xué)”,全國(guó)有兩所工業(yè)名校——哈工大和合工大。
哈爾濱,明顯我爺是走不過(guò)去,那就選合工大。多年后我第一次去哈爾濱,堅(jiān)持要去哈工大看看,仿佛完成我爹的一個(gè)心愿。
哈工大挺神奇,校區(qū)被一條大馬路割成兩塊,沿圍墻走半天,也只能從側(cè)門進(jìn)入校區(qū),漂亮的大門正對(duì)著車水馬龍的馬路,想拍個(gè)全影得站馬路中間,罷了。傍晚,我在校園遛半天,抓了一哈工大學(xué)子問(wèn):“你們學(xué)校有沒啥景點(diǎn)可參觀?”那娃笑了半天,“我們學(xué)校只有宿舍和教學(xué)樓”。還是在哈工大食堂邊發(fā)現(xiàn)一家小小文創(chuàng)店,哈工大的文創(chuàng),全是衛(wèi)星和導(dǎo)彈,牛不牛?!
哈工大一直不是教育部直屬的高校,原來(lái)隸屬于國(guó)防科工委,現(xiàn)今隸屬于國(guó)家工信部,是一所有軍工和國(guó)防科技背景的高校,是公認(rèn)的“國(guó)防七子之首”。打個(gè)比喻,哈工大于哈爾濱,有點(diǎn)像中科大于合肥,低調(diào)到陌生。
有幾年,走南闖北,最喜歡坐兩家航司航班,一家山東航空,另一家龍江航空。山航真的極少延誤,經(jīng)常延半小時(shí),提前十分鐘給你落地,讓人懷疑機(jī)長(zhǎng)們是不是組團(tuán)去俄羅斯留過(guò)學(xué)。
喜歡龍江航空,是因?yàn)榧词菇?jīng)濟(jì)艙座位也極寬敞,大約為了配合東北大高個(gè)。據(jù)個(gè)人經(jīng)驗(yàn),龍江航空的空姐空少們,身材最挺拔,顏值最高,洋氣。
哈爾濱是中東鐵路重要的交通樞紐,自然成了商貿(mào)聚集地。加之清政府對(duì)東北開禁,中原人開始“闖關(guān)東”,哈爾濱人口不斷增長(zhǎng),國(guó)際性商埠的近代城市雛形日益顯現(xiàn)。
哈爾濱作為這條鐵路線上的最大城市,吸引來(lái)更多外國(guó)人。先后有33個(gè)國(guó)家16萬(wàn)余僑民聚集這里,19個(gè)國(guó)家在此設(shè)立領(lǐng)事館,各種風(fēng)格的建筑拔地而起。哈爾濱曾是當(dāng)時(shí)的北滿經(jīng)濟(jì)中心和重要的國(guó)際都市之一。
哈爾濱一直有“東方莫斯科”和“東方小巴黎”之稱。只是在過(guò)去的30年,東北發(fā)展出現(xiàn)斷崖式滑坡,作為七普期間全國(guó)唯一一個(gè)人口負(fù)增長(zhǎng)的省會(huì),哈爾濱常住人口從最高點(diǎn)的1100萬(wàn),到2021年跌破千萬(wàn)大關(guān),東北再無(wú)千萬(wàn)人口大城市。
今年冬天這波潑天的富貴,不是爾濱總算學(xué)會(huì)了切凍梨,而是全國(guó)人民重新發(fā)現(xiàn)爾濱之美。
2019年夏天,第一次去哈爾濱。那年索菲亞大教堂在檢修,沒能進(jìn)去。夏天的傍晚,教堂廣場(chǎng)上的噴泉很漂亮,還有一陣一陣的白鴿。正瞎轉(zhuǎn)悠,看見一支西洋樂隊(duì),穿著正式演出服,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曲子。旁邊站了一圈穿汗衫和大褲衩的當(dāng)?shù)匕傩铡?戳伺赃叺慕榻B才知,每年夏天都有哈爾濱之夏的小型音樂會(huì),在廣場(chǎng)上不定期演出。
晚上去逛中央大街,滿街都是墨綠色的馬迭爾冰棒車,買一根,一路啃一路逛到防洪紀(jì)念塔,路上有很多給游客畫碳素畫、素描畫的小攤,那些攤主的氣質(zhì)也非常藝術(shù)家,間或還有人坐在那里演奏小提琴,那一瞬,好像重回巴黎小丘廣場(chǎng)。
哈爾濱真的是個(gè)特別美好的城市,有著老錢風(fēng)的優(yōu)雅。
前幾天翻到一條短視頻,那個(gè)做索菲亞大教堂蛋糕的姑娘,錄視頻時(shí)哭得稀里嘩啦,“真的只有哈爾濱人才懂”,“也不是因?yàn)榈案馍庾兒昧瞬趴?而是看到自己的城市變好了,真的很開心”。
我的眼眶也跟著紅了,為她,為她的城市開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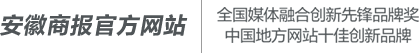
 設(shè)為首頁(yè)
設(shè)為首頁(yè)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(lián)系我們
聯(lián)系我們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