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餐一碗小米粥,一只煮蛋,幾片鹵牛肉,一小把花生米,愈兩周。
近日,味蕾漸漸起了厭倦,身體發出強烈信號——我知道,大米粥的癮又犯了。東北大米適量,電力鍋壓好,盛出一碗,茸茸白白,筷子尖挑一撮,有拉絲感。低頭喝一口,無上滿足,堪比珍饈美饌。大米粥的醇厚綿柔洇染著特有的米香,淡淡淺淺,遠了又近了,時隱時現著,令時光倒流,一頭撲向溫暖童年。一碗大米粥,被我無比渴慕地享用著,直至額上微汗,內心一片寧靜,如聽梵音,如在深山。
兒時,大病初愈,我母親文火慢熬一鍋米粥,盛一碗到床前。出于求生本能的我,強撐著爬起,耷拉著滯重頭顱,淺淺抿一口,病,一霎時好了大半。這一碗米粥,似乎給予我千斤之力,它的精魂托舉著我,沉重的身體頓時輕松起來了。喝完一碗,還想第二碗。彼時,鄉下稻米不曾被拋光打蠟,帶著粗樸的角質層,大灶柴火煮出來,結厚厚一層粥油,殊為養人。
成長于長江中下游平原的人們,身體基因里注定鐫刻著稻米的鄉愁,走到哪兒,始終不曾改變。良渚文化遺址,出土過一把一把碳化水稻,科學家運用同位素檢測出,這些稻谷距今四五千年矣。意味著我們的祖先,于新石器時代,便開始了野生水稻的馴化,當真了不起。
一次,看一部美食紀錄片,美國印第安原居民至今保留著烹食野生菰米的傳統習慣。這種野生植物,喜水,生長于湖泊淺灘,因植株稀疏,無法一把把收割稻禾。當菰米谷粒飽滿植株漸黃,印第安人劃著兩頭尖翹而中間寬敞的小木船,前后兩人,一人負責劃船于稻禾之中,一人手持長棍,左右互搏地敲打木船兩邊的菰米穗子,如是,菰米谷粒紛紛落至敞開的船艙。
也有相當一部分谷粒落入水中。翌年春,發芽生根,開花結果,再去采收……年復一年,無窮盡矣。
菰米谷粒運回家,倒入一種古老木槽,以木槌舂之,揚其谷殼,剩下窄而長的菰米粒。彼時,全家一定有一頓菰米飯享用。
中國自古也產菰米。得益于農業科學家的培育,自野生慢慢過渡至育種、栽培階段。囿于產量不能突破等諸多因素,并非大面積推廣。因產量少極,目前依然停留于禮品贈送階段。
早幾年,恩師曾經贈我幾盒菰米,初一月牙般窄小,玲瓏而美,氣質卓絕,亮晶晶散發微光。作為食物吃下去,當真罪過——這菰米應放在水晶瓶內陳列起來,漂亮至極。煮成的米飯,口感超好。
牡丹江籍作家高艷女史也曾千里迢遙寄贈過一箱石板大米來。我糊涂地烹飯煮粥,波瀾不驚吃下去了。前年,在上海的一次晚宴上,被高艷恩師告知,這種火山灰巖田產出的石板大米,名聞遐邇,極其稀罕,價值兩三千不等……望著眼前這小巧倩兮的女子,卻有著如此一顆慷慨之心,當真舍得呀。大抵也是別人饋贈與她的,竟寄給我們了。
何德何能啊——我倆僅僅一面之緣。
說回開頭,我喝小米粥,不過是迫于減重需要。小米隸屬雜糧系列,既然無法戒除碳水,高粱、玉米等雜糧更是難以下咽,唯有選擇小米。砂罐熬煮,滾水下米,頂沸,小火燜五分鐘,再中火,直至水米交融,大約十五分鐘便好。方便是方便,可惜,始終吃不出大米的綿厚香醇。易消化,一會兒,便餓了。
自菜市買回合肥這邊特有的米團,每次小米粥快煮好時,搭半只米團進去,充饑,抵飽。吃來吃去,依然十足碳水。
酷夏,去山東采風。一個周末,酒店用早餐,恰好與一對母子同桌,他們大約自縣里來海邊小城度假。瘦弱不堪的小男孩沉浸在他母親盛來的小米粥里,一碗接一碗,且發出滿足的哼哼之聲,菜也不夾一筷子。孩子粗生放養慣了,手里捏一只饅頭,吃得甘之如飴……
看得我心疼不已,顧不上矜持以及邊界感,悄悄勸那位年輕母親,給孩子盛杯牛奶吧,補鈣。年輕母親不以為意,對我笑笑,一口樸素的山東方言:沒事,小米粥有營養。我自覺多事,也唐突了,原本萍水相逢。
自古說小米養胃。但,西醫認為,這樣的粥易消化,長期喝,反而對胃不好,僅僅一點點碳水化合物而已,無任何實質性營養可言。維持機體平衡最重要的一項,則是蛋白質。故,要多攝入肉蛋奶,才能營養均衡。當然,谷物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種。
我們老一輩幾乎都是在這樣平易的碳水里跌打滾爬過來的,字典里不曾有過營養均衡的概念。畢竟中國人吃飽飯的日子,也才剛剛三十余年。
合肥這邊的米團,并非如江浙那邊的長條型年糕,而是手工制作出的圓錐體,有著稻米濃烈的香氣,聞之,可刺激旺盛的食欲。買一點兒回家,清水儲養,三兩日換一次水,一烹即熟,不可久煮,否則會失去彈牙口感,別無嚼勁。
常因寫稿,誤了午餐,餓極,冰箱里有什么,吃什么。一次,扒拉出八個餃子,考慮營養均衡,又下了四五魚丸。末了,吃下五個餃子,再也不想繼續進餐。飽了?似乎沒有,就是純粹不愛面食,吞不下。這一餐吃得意興闌珊,一下午,整個身體皆不得勁。晚餐,煮了一罐粳米菜粥,搭配幾兩肉末。剩下的三個餃子煎至焦黃脆香,也只勉強吃了一個,我要空出胃口饕餮菜粥。一碗食罄,尚不解饞,又添半碗,獨獨一瓶黃豆西瓜醬,間或以筷尖蘸一點兒。
一餐攝入的均是巨量碳水,一種來自原始的暖老溫貧的滿足感,勝過一切豪華盛宴。
年歲愈長,愈回歸童年胃口了。味蕾有著頑強記憶,它一點點提示著肉身,應該葉落歸根了,回到生命誕生的最初之地享用稻米。
近日,凄風苦雨,童年的日子頻頻閃回,憶之溫暖,感念久之。
這樣的臘月,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皖南地區,一村村婦女們無一例外地開始了忙碌,分明是一場場圍繞大米的狂歡盛典——也不過是一份口腹之欲,給孩子們準備的過年零食。
一切皆圍繞著稻米做文章,在一個盛產稻米的丘陵地區,再也不能翻新出別的花樣。
秈米浸泡一日一宿后,雙手插進濕淋淋米堆,捧起,搓一搓,一粒粒飽漲的大米閃著熒光,潔白如霜,甚是愛惜,連淘米水也不浪費,倒入灶頭吊罐,溫熱,摻點山芋剩粥米糠,喂了豬。
石磨早已清洗干凈,靜等大米一勺勺被填入磨眼,磨成源遠流長的玉液瓊漿,晃晃悠悠挑回家。灶房木柴堆得山高,接下來攤坯。對,攤坯,吾鄉向來如是稱呼,“坯”念三聲。
大鍋內沸水翻騰,廚房霧氣彌漫。挖滿滿一勺米漿,倒入一只特制的鐵盤內,晃勻,漂與沸水上,蓋上鍋蓋,不及一分鐘,米漿熟而凝固,輕輕揭下,薄如蟬翼,香氣撲鼻。這種被蒸熟的米制食品,廣東地區叫腸粉,澆上特質醬油,即熟即食。
吾鄉并非如此吃法,將之曬成半干,剪至長條,斜裁成三角狀,繼續攤開于竹簸箕里晾曬,直至脆干,備用。曬干的坯子又有了另一筆名——米角子。
黑砂置鐵鍋中炒至起青煙,挖一瓢曬干的米角子,丟入滾燙黑砂中翻炒,米角子遇熱迅速膨脹,直至焦黃,入嘴嘎嚓有聲,愈吃愈上癮。
講究的人家事先在米漿里摻一把黑芝麻,炒熟的米角子,嚼起來更香。我母親向來節儉,她斷斷不肯加上芝麻。地里收獲的一點芝麻,只能用作正月十五的湯圓餡這一途。
也是寒冬臘月,我去村南頭的小米家串門。她奶奶一見著我,一雙小腳顫顫巍巍的,漂移到里屋,抓出一大把炒好的米角子賞賜我。那是我吃到過的最胖大最喧香的米角子。
小米姑姑的女兒左玲與我小學同學,待人真摯。左玲每次來外婆家,遠遠在路上遇見了,總是大喊我的名字——但凡左玲手里攥三只菱角,總要遞上兩只與我。她潔白的牙齒笑起來閃閃亮的樣子,至今猶記。
左玲的外婆,正是小米的奶奶。
一入了冬,總能在合肥菜市邂逅售賣麻糖、小糖餅子的小販,兩只竹篾編的扁圓筐子,一頭麻糖,一頭糖餅子。作為極其古老的一種鄉村零食,二者齊齊散發著滄桑的年代感。一見著它們,條件反射般垂涎欲滴,清甜滋味昔日重來,要走很長很長的一段人生路,方可抵達逝去了的遙遠年代。
每次遇見,總要買一點兒糖餅子。捻一塊擱嘴里,不要咀嚼,一直含著它,慢慢地,相融于唾液,由金剛鐵化作了繞指柔,用舌頭將它翻個身,繼續含著……這種來自稻米精魂的甜,鋪天蓋地而來,眼前一片白衣勝雪,這漫無邊際的雪花正一點點氤氳著口腔味蕾,直至迎來一個七彩童年。
一整座村莊的孩子,沒有誰不曾偷過家里的米。悄悄放布袋里,一路拎著,結伴步行很遠的辛苦路,到達一座叫做橫埠河的集鎮,翻一座山,一座神秘的小小村落,忽現目前。
這個村子里,幾乎家家生意人,一律加工糖餅子售賣。我們小孩沒有錢去買,唯有偷米去換。
陌生村莊的生意人,真會拿捏孩子們呢,半布袋白花花的大米拎過去,只能換回一點點糖餅子,到底也滿足了。回家路上想著,堅決不能吃掉。實在饞極,僅僅摸一塊出來含著,直想著回村賣給小伙伴換幾分錢。到底,每個孩子流感一樣相互傳染,皆背著大人將米偷出來,去換。那些糖餅子,最終陸續進了我們各自的胃。那種為獲得一點甜的口腔滿足,而深感內疚自責的矛盾心理,實在折磨人。
慢慢地,我們再也不曾去到那座陌生村莊。這一份適可而止的童心里,一定有著對于大米的珍惜。
這些不可多得的甜蜜,令童年的日月無比珍貴。彼時,縱然窮乏貧瘠,隨之光陰的發酵,到得當下,終成琥珀,值得捧起來呵護——有著稻米之甜的童年,簡直是可歌可泣的,依然被我熱愛著。它一直在長江中下游平原游蕩,不盈不虧,如明月照著大地。
(錢紅麗
)
【橙美文】明月照著大地
安徽商報
張雪子
2023-12-18 09:51:40
早餐一碗小米粥,一只煮蛋,幾片鹵牛肉,一小把花生米,愈兩周。
近日,味蕾漸漸起了厭倦,身體發出強烈信號——我知道,大米粥的癮又犯了。東北大米適量,電力鍋壓好,盛出一碗,茸茸白白,筷子尖挑一撮,有拉絲感。低頭喝一口,無上滿足,堪比珍饈美饌。大米粥的醇厚綿柔洇染著特有的米香,淡淡淺淺,遠了又近了,時隱時現著,令時光倒流,一頭撲向溫暖童年。一碗大米粥,被我無比渴慕地享用著,直至額上微汗,內心一片寧靜,如聽梵音,如在深山。
兒時,大病初愈,我母親文火慢熬一鍋米粥,盛一碗到床前。出于求生本能的我,強撐著爬起,耷拉著滯重頭顱,淺淺抿一口,病,一霎時好了大半。這一碗米粥,似乎給予我千斤之力,它的精魂托舉著我,沉重的身體頓時輕松起來了。喝完一碗,還想第二碗。彼時,鄉下稻米不曾被拋光打蠟,帶著粗樸的角質層,大灶柴火煮出來,結厚厚一層粥油,殊為養人。
成長于長江中下游平原的人們,身體基因里注定鐫刻著稻米的鄉愁,走到哪兒,始終不曾改變。良渚文化遺址,出土過一把一把碳化水稻,科學家運用同位素檢測出,這些稻谷距今四五千年矣。意味著我們的祖先,于新石器時代,便開始了野生水稻的馴化,當真了不起。
一次,看一部美食紀錄片,美國印第安原居民至今保留著烹食野生菰米的傳統習慣。這種野生植物,喜水,生長于湖泊淺灘,因植株稀疏,無法一把把收割稻禾。當菰米谷粒飽滿植株漸黃,印第安人劃著兩頭尖翹而中間寬敞的小木船,前后兩人,一人負責劃船于稻禾之中,一人手持長棍,左右互搏地敲打木船兩邊的菰米穗子,如是,菰米谷粒紛紛落至敞開的船艙。
也有相當一部分谷粒落入水中。翌年春,發芽生根,開花結果,再去采收……年復一年,無窮盡矣。
菰米谷粒運回家,倒入一種古老木槽,以木槌舂之,揚其谷殼,剩下窄而長的菰米粒。彼時,全家一定有一頓菰米飯享用。
中國自古也產菰米。得益于農業科學家的培育,自野生慢慢過渡至育種、栽培階段。囿于產量不能突破等諸多因素,并非大面積推廣。因產量少極,目前依然停留于禮品贈送階段。
早幾年,恩師曾經贈我幾盒菰米,初一月牙般窄小,玲瓏而美,氣質卓絕,亮晶晶散發微光。作為食物吃下去,當真罪過——這菰米應放在水晶瓶內陳列起來,漂亮至極。煮成的米飯,口感超好。
牡丹江籍作家高艷女史也曾千里迢遙寄贈過一箱石板大米來。我糊涂地烹飯煮粥,波瀾不驚吃下去了。前年,在上海的一次晚宴上,被高艷恩師告知,這種火山灰巖田產出的石板大米,名聞遐邇,極其稀罕,價值兩三千不等……望著眼前這小巧倩兮的女子,卻有著如此一顆慷慨之心,當真舍得呀。大抵也是別人饋贈與她的,竟寄給我們了。
何德何能啊——我倆僅僅一面之緣。
說回開頭,我喝小米粥,不過是迫于減重需要。小米隸屬雜糧系列,既然無法戒除碳水,高粱、玉米等雜糧更是難以下咽,唯有選擇小米。砂罐熬煮,滾水下米,頂沸,小火燜五分鐘,再中火,直至水米交融,大約十五分鐘便好。方便是方便,可惜,始終吃不出大米的綿厚香醇。易消化,一會兒,便餓了。
自菜市買回合肥這邊特有的米團,每次小米粥快煮好時,搭半只米團進去,充饑,抵飽。吃來吃去,依然十足碳水。
酷夏,去山東采風。一個周末,酒店用早餐,恰好與一對母子同桌,他們大約自縣里來海邊小城度假。瘦弱不堪的小男孩沉浸在他母親盛來的小米粥里,一碗接一碗,且發出滿足的哼哼之聲,菜也不夾一筷子。孩子粗生放養慣了,手里捏一只饅頭,吃得甘之如飴……
看得我心疼不已,顧不上矜持以及邊界感,悄悄勸那位年輕母親,給孩子盛杯牛奶吧,補鈣。年輕母親不以為意,對我笑笑,一口樸素的山東方言:沒事,小米粥有營養。我自覺多事,也唐突了,原本萍水相逢。
自古說小米養胃。但,西醫認為,這樣的粥易消化,長期喝,反而對胃不好,僅僅一點點碳水化合物而已,無任何實質性營養可言。維持機體平衡最重要的一項,則是蛋白質。故,要多攝入肉蛋奶,才能營養均衡。當然,谷物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種。
我們老一輩幾乎都是在這樣平易的碳水里跌打滾爬過來的,字典里不曾有過營養均衡的概念。畢竟中國人吃飽飯的日子,也才剛剛三十余年。
合肥這邊的米團,并非如江浙那邊的長條型年糕,而是手工制作出的圓錐體,有著稻米濃烈的香氣,聞之,可刺激旺盛的食欲。買一點兒回家,清水儲養,三兩日換一次水,一烹即熟,不可久煮,否則會失去彈牙口感,別無嚼勁。
常因寫稿,誤了午餐,餓極,冰箱里有什么,吃什么。一次,扒拉出八個餃子,考慮營養均衡,又下了四五魚丸。末了,吃下五個餃子,再也不想繼續進餐。飽了?似乎沒有,就是純粹不愛面食,吞不下。這一餐吃得意興闌珊,一下午,整個身體皆不得勁。晚餐,煮了一罐粳米菜粥,搭配幾兩肉末。剩下的三個餃子煎至焦黃脆香,也只勉強吃了一個,我要空出胃口饕餮菜粥。一碗食罄,尚不解饞,又添半碗,獨獨一瓶黃豆西瓜醬,間或以筷尖蘸一點兒。
一餐攝入的均是巨量碳水,一種來自原始的暖老溫貧的滿足感,勝過一切豪華盛宴。
年歲愈長,愈回歸童年胃口了。味蕾有著頑強記憶,它一點點提示著肉身,應該葉落歸根了,回到生命誕生的最初之地享用稻米。
近日,凄風苦雨,童年的日子頻頻閃回,憶之溫暖,感念久之。
這樣的臘月,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皖南地區,一村村婦女們無一例外地開始了忙碌,分明是一場場圍繞大米的狂歡盛典——也不過是一份口腹之欲,給孩子們準備的過年零食。
一切皆圍繞著稻米做文章,在一個盛產稻米的丘陵地區,再也不能翻新出別的花樣。
秈米浸泡一日一宿后,雙手插進濕淋淋米堆,捧起,搓一搓,一粒粒飽漲的大米閃著熒光,潔白如霜,甚是愛惜,連淘米水也不浪費,倒入灶頭吊罐,溫熱,摻點山芋剩粥米糠,喂了豬。
石磨早已清洗干凈,靜等大米一勺勺被填入磨眼,磨成源遠流長的玉液瓊漿,晃晃悠悠挑回家。灶房木柴堆得山高,接下來攤坯。對,攤坯,吾鄉向來如是稱呼,“坯”念三聲。
大鍋內沸水翻騰,廚房霧氣彌漫。挖滿滿一勺米漿,倒入一只特制的鐵盤內,晃勻,漂與沸水上,蓋上鍋蓋,不及一分鐘,米漿熟而凝固,輕輕揭下,薄如蟬翼,香氣撲鼻。這種被蒸熟的米制食品,廣東地區叫腸粉,澆上特質醬油,即熟即食。
吾鄉并非如此吃法,將之曬成半干,剪至長條,斜裁成三角狀,繼續攤開于竹簸箕里晾曬,直至脆干,備用。曬干的坯子又有了另一筆名——米角子。
黑砂置鐵鍋中炒至起青煙,挖一瓢曬干的米角子,丟入滾燙黑砂中翻炒,米角子遇熱迅速膨脹,直至焦黃,入嘴嘎嚓有聲,愈吃愈上癮。
講究的人家事先在米漿里摻一把黑芝麻,炒熟的米角子,嚼起來更香。我母親向來節儉,她斷斷不肯加上芝麻。地里收獲的一點芝麻,只能用作正月十五的湯圓餡這一途。
也是寒冬臘月,我去村南頭的小米家串門。她奶奶一見著我,一雙小腳顫顫巍巍的,漂移到里屋,抓出一大把炒好的米角子賞賜我。那是我吃到過的最胖大最喧香的米角子。
小米姑姑的女兒左玲與我小學同學,待人真摯。左玲每次來外婆家,遠遠在路上遇見了,總是大喊我的名字——但凡左玲手里攥三只菱角,總要遞上兩只與我。她潔白的牙齒笑起來閃閃亮的樣子,至今猶記。
左玲的外婆,正是小米的奶奶。
一入了冬,總能在合肥菜市邂逅售賣麻糖、小糖餅子的小販,兩只竹篾編的扁圓筐子,一頭麻糖,一頭糖餅子。作為極其古老的一種鄉村零食,二者齊齊散發著滄桑的年代感。一見著它們,條件反射般垂涎欲滴,清甜滋味昔日重來,要走很長很長的一段人生路,方可抵達逝去了的遙遠年代。
每次遇見,總要買一點兒糖餅子。捻一塊擱嘴里,不要咀嚼,一直含著它,慢慢地,相融于唾液,由金剛鐵化作了繞指柔,用舌頭將它翻個身,繼續含著……這種來自稻米精魂的甜,鋪天蓋地而來,眼前一片白衣勝雪,這漫無邊際的雪花正一點點氤氳著口腔味蕾,直至迎來一個七彩童年。
一整座村莊的孩子,沒有誰不曾偷過家里的米。悄悄放布袋里,一路拎著,結伴步行很遠的辛苦路,到達一座叫做橫埠河的集鎮,翻一座山,一座神秘的小小村落,忽現目前。
這個村子里,幾乎家家生意人,一律加工糖餅子售賣。我們小孩沒有錢去買,唯有偷米去換。
陌生村莊的生意人,真會拿捏孩子們呢,半布袋白花花的大米拎過去,只能換回一點點糖餅子,到底也滿足了。回家路上想著,堅決不能吃掉。實在饞極,僅僅摸一塊出來含著,直想著回村賣給小伙伴換幾分錢。到底,每個孩子流感一樣相互傳染,皆背著大人將米偷出來,去換。那些糖餅子,最終陸續進了我們各自的胃。那種為獲得一點甜的口腔滿足,而深感內疚自責的矛盾心理,實在折磨人。
慢慢地,我們再也不曾去到那座陌生村莊。這一份適可而止的童心里,一定有著對于大米的珍惜。
這些不可多得的甜蜜,令童年的日月無比珍貴。彼時,縱然窮乏貧瘠,隨之光陰的發酵,到得當下,終成琥珀,值得捧起來呵護——有著稻米之甜的童年,簡直是可歌可泣的,依然被我熱愛著。它一直在長江中下游平原游蕩,不盈不虧,如明月照著大地。
(錢紅麗
)
早餐一碗小米粥,一只煮蛋,幾片鹵牛肉,一小把花生米,愈兩周。近日,味蕾漸漸起了厭倦,身體發出強烈信號——我知道,大米粥的癮又犯了。東北大米適量,電力鍋壓好,盛出一碗,茸茸白白,筷子尖挑一撮,有拉絲感。低頭喝一口,無上滿足,堪比珍饈美饌。大米粥的醇厚綿柔洇染著特有的米香,淡淡淺淺,遠了又近了,時隱時現著,令時光倒流,一頭撲向溫暖童年。一碗大米粥,被我無比渴慕地享用著,直至額上微汗,內心一片寧靜,如聽梵音,如在深山。兒時,大病初愈,我母親文火慢熬一鍋米粥,盛一碗到床前。出于求生本能的我,強撐著爬起,耷拉著滯重頭顱,淺淺抿一口,病,一霎時好了大半。這一碗米粥,似乎給予我千斤之力,它的精魂托舉著我,沉重的身體頓時輕松起來了。喝完一碗,還想第二碗。彼時,鄉下稻米不曾被拋光打蠟,帶著粗樸的角質層,大灶柴火煮出來,結厚厚一層粥油,殊為養人。成長于長江中下游平原的人們,身體基因里注定鐫刻著稻米的鄉愁,走到哪兒,始終不曾改變。良渚文化遺址,出土過一把一把碳化水稻,科學家運用同位素檢測出,這些稻谷距今四五千年矣。意味著我們的祖先,于新石器時代,便開始了野生水稻的馴化,當真了不起。一次,看一部美食紀錄片,美國印第安原居民至今保留著烹食野生菰米的傳統習慣。這種野生植物,喜水,生長于湖泊淺灘,因植株稀疏,無法一把把收割稻禾。當菰米谷粒飽滿植株漸黃,印第安人劃著兩頭尖翹而中間寬敞的小木船,前后兩人,一人負責劃船于稻禾之中,一人手持長棍,左右互搏地敲打木船兩邊的菰米穗子,如是,菰米谷粒紛紛落至敞開的船艙。也有相當一部分谷粒落入水中。翌年春,發芽生根,開花結果,再去采收……年復一年,無窮盡矣。菰米谷粒運回家,倒入一種古老木槽,以木槌舂之,揚其谷殼,剩下窄而長的菰米粒。彼時,全家一定有一頓菰米飯享用。中國自古也產菰米。得益于農業科學家的培育,自野生慢慢過渡至育種、栽培階段。囿于產量不能突破等諸多因素,并非大面積推廣。因產量少極,目前依然停留于禮品贈送階段。早幾年,恩師曾經贈我幾盒菰米,初一月牙般窄小,玲瓏而美,氣質卓絕,亮晶晶散發微光。作為食物吃下去,當真罪過——這菰米應放在水晶瓶內陳列起來,漂亮至極。煮成的米飯,口感超好。牡丹江籍作家高艷女史也曾千里迢遙寄贈過一箱石板大米來。我糊涂地烹飯煮粥,波瀾不驚吃下去了。前年,在上海的一次晚宴上,被高艷恩師告知,這種火山灰巖田產出的石板大米,名聞遐邇,極其稀罕,價值兩三千不等……望著眼前這小巧倩兮的女子,卻有著如此一顆慷慨之心,當真舍得呀。大抵也是別人饋贈與她的,竟寄給我們了。何德何能啊——我倆僅僅一面之緣。說回開頭,我喝小米粥,不過是迫于減重需要。小米隸屬雜糧系列,既然無法戒除碳水,高粱、玉米等雜糧更是難以下咽,唯有選擇小米。砂罐熬煮,滾水下米,頂沸,小火燜五分鐘,再中火,直至水米交融,大約十五分鐘便好。方便是方便,可惜,始終吃不出大米的綿厚香醇。易消化,一會兒,便餓了。自菜市買回合肥這邊特有的米團,每次小米粥快煮好時,搭半只米團進去,充饑,抵飽。吃來吃去,依然十足碳水。酷夏,去山東采風。一個周末,酒店用早餐,恰好與一對母子同桌,他們大約自縣里來海邊小城度假。瘦弱不堪的小男孩沉浸在他母親盛來的小米粥里,一碗接一碗,且發出滿足的哼哼之聲,菜也不夾一筷子。孩子粗生放養慣了,手里捏一只饅頭,吃得甘之如飴……看得我心疼不已,顧不上矜持以及邊界感,悄悄勸那位年輕母親,給孩子盛杯牛奶吧,補鈣。年輕母親不以為意,對我笑笑,一口樸素的山東方言:沒事,小米粥有營養。我自覺多事,也唐突了,原本萍水相逢。自古說小米養胃。但,西醫認為,這樣的粥易消化,長期喝,反而對胃不好,僅僅一點點碳水化合物而已,無任何實質性營養可言。維持機體平衡最重要的一項,則是蛋白質。故,要多攝入肉蛋奶,才能營養均衡。當然,谷物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種。我們老一輩幾乎都是在這樣平易的碳水里跌打滾爬過來的,字典里不曾有過營養均衡的概念。畢竟中國人吃飽飯的日子,也才剛剛三十余年。合肥這邊的米團,并非如江浙那邊的長條型年糕,而是手工制作出的圓錐體,有著稻米濃烈的香氣,聞之,可刺激旺盛的食欲。買一點兒回家,清水儲養,三兩日換一次水,一烹即熟,不可久煮,否則會失去彈牙口感,別無嚼勁。常因寫稿,誤了午餐,餓極,冰箱里有什么,吃什么。一次,扒拉出八個餃子,考慮營養均衡,又下了四五魚丸。末了,吃下五個餃子,再也不想繼續進餐。飽了?似乎沒有,就是純粹不愛面食,吞不下。這一餐吃得意興闌珊,一下午,整個身體皆不得勁。晚餐,煮了一罐粳米菜粥,搭配幾兩肉末。剩下的三個餃子煎至焦黃脆香,也只勉強吃了一個,我要空出胃口饕餮菜粥。一碗食罄,尚不解饞,又添半碗,獨獨一瓶黃豆西瓜醬,間或以筷尖蘸一點兒。一餐攝入的均是巨量碳水,一種來自原始的暖老溫貧的滿足感,勝過一切豪華盛宴。年歲愈長,愈回歸童年胃口了。味蕾有著頑強記憶,它一點點提示著肉身,應該葉落歸根了,回到生命誕生的最初之地享用稻米。近日,凄風苦雨,童年的日子頻頻閃回,憶之溫暖,感念久之。這樣的臘月,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皖南地區,一村村婦女們無一例外地開始了忙碌,分明是一場場圍繞大米的狂歡盛典——也不過是一份口腹之欲,給孩子們準備的過年零食。一切皆圍繞著稻米做文章,在一個盛產稻米的丘陵地區,再也不能翻新出別的花樣。秈米浸泡一日一宿后,雙手插進濕淋淋米堆,捧起,搓一搓,一粒粒飽漲的大米閃著熒光,潔白如霜,甚是愛惜,連淘米水也不浪費,倒入灶頭吊罐,溫熱,摻點山芋剩粥米糠,喂了豬。石磨早已清洗干凈,靜等大米一勺勺被填入磨眼,磨成源遠流長的玉液瓊漿,晃晃悠悠挑回家。灶房木柴堆得山高,接下來攤坯。對,攤坯,吾鄉向來如是稱呼,“坯”念三聲。大鍋內沸水翻騰,廚房霧氣彌漫。挖滿滿一勺米漿,倒入一只特制的鐵盤內,晃勻,漂與沸水上,蓋上鍋蓋,不及一分鐘,米漿熟而凝固,輕輕揭下,薄如蟬翼,香氣撲鼻。這種被蒸熟的米制食品,廣東地區叫腸粉,澆上特質醬油,即熟即食。吾鄉并非如此吃法,將之曬成半干,剪至長條,斜裁成三角狀,繼續攤開于竹簸箕里晾曬,直至脆干,備用。曬干的坯子又有了另一筆名——米角子。黑砂置鐵鍋中炒至起青煙,挖一瓢曬干的米角子,丟入滾燙黑砂中翻炒,米角子遇熱迅速膨脹,直至焦黃,入嘴嘎嚓有聲,愈吃愈上癮。講究的人家事先在米漿里摻一把黑芝麻,炒熟的米角子,嚼起來更香。我母親向來節儉,她斷斷不肯加上芝麻。地里收獲的一點芝麻,只能用作正月十五的湯圓餡這一途。也是寒冬臘月,我去村南頭的小米家串門。她奶奶一見著我,一雙小腳顫顫巍巍的,漂移到里屋,抓出一大把炒好的米角子賞賜我。那是我吃到過的最胖大最喧香的米角子。小米姑姑的女兒左玲與我小學同學,待人真摯。左玲每次來外婆家,遠遠在路上遇見了,總是大喊我的名字——但凡左玲手里攥三只菱角,總要遞上兩只與我。她潔白的牙齒笑起來閃閃亮的樣子,至今猶記。左玲的外婆,正是小米的奶奶。一入了冬,總能在合肥菜市邂逅售賣麻糖、小糖餅子的小販,兩只竹篾編的扁圓筐子,一頭麻糖,一頭糖餅子。作為極其古老的一種鄉村零食,二者齊齊散發著滄桑的年代感。一見著它們,條件反射般垂涎欲滴,清甜滋味昔日重來,要走很長很長的一段人生路,方可抵達逝去了的遙遠年代。每次遇見,總要買一點兒糖餅子。捻一塊擱嘴里,不要咀嚼,一直含著它,慢慢地,相融于唾液,由金剛鐵化作了繞指柔,用舌頭將它翻個身,繼續含著……這種來自稻米精魂的甜,鋪天蓋地而來,眼前一片白衣勝雪,這漫無邊際的雪花正一點點氤氳著口腔味蕾,直至迎來一個七彩童年。一整座村莊的孩子,沒有誰不曾偷過家里的米。悄悄放布袋里,一路拎著,結伴步行很遠的辛苦路,到達一座叫做橫埠河的集鎮,翻一座山,一座神秘的小小村落,忽現目前。這個村子里,幾乎家家生意人,一律加工糖餅子售賣。我們小孩沒有錢去買,唯有偷米去換。陌生村莊的生意人,真會拿捏孩子們呢,半布袋白花花的大米拎過去,只能換回一點點糖餅子,到底也滿足了。回家路上想著,堅決不能吃掉。實在饞極,僅僅摸一塊出來含著,直想著回村賣給小伙伴換幾分錢。到底,每個孩子流感一樣相互傳染,皆背著大人將米偷出來,去換。那些糖餅子,最終陸續進了我們各自的胃。那種為獲得一點甜的口腔滿足,而深感內疚自責的矛盾心理,實在折磨人。慢慢地,我們再也不曾去到那座陌生村莊。這一份適可而止的童心里,一定有著對于大米的珍惜。這些不可多得的甜蜜,令童年的日月無比珍貴。彼時,縱然窮乏貧瘠,隨之光陰的發酵,到得當下,終成琥珀,值得捧起來呵護——有著稻米之甜的童年,簡直是可歌可泣的,依然被我熱愛著。它一直在長江中下游平原游蕩,不盈不虧,如明月照著大地。(錢紅麗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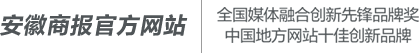
 設為首頁
設為首頁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系我們
聯系我們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