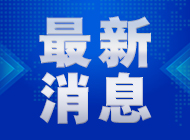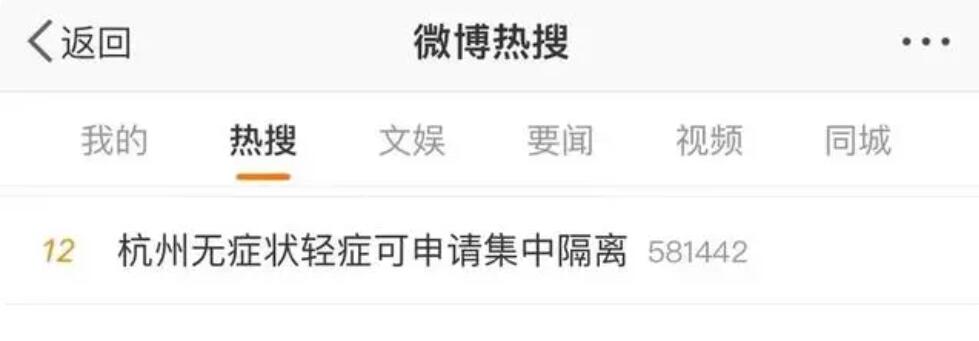樓蘭與精絕
◎楊菁菁
兩天讀完王炳華寫的《懸念樓蘭-精絕》,這套書出版于2012年,以“親歷”考古為旨,是真正的考古大家們寫的科普之作。除樓蘭精絕古城之外,這套書還包含探秘曾侯乙墓、滿城漢墓、馬王堆漢墓、敦煌石窟寺,都是親歷者與守護者作的文,其專業度與分量,與市面上常見的二手知識不可同日而語。書已不再版,這套書中有幾本在市面上流通的價格,九五品,已數倍于定價。好不容易買到手,一氣讀完,宛如受到了精神灌溉。
初識樓蘭是在《漢書》中。與其他西域小國相比,關于樓蘭筆墨頗多。《漢書·西域傳》載:“鄯善國,本名樓蘭,王治扜泥城,去陽關千六百里,去長安六千一百里。戶千五百七十,口萬四千一百,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。輔國侯、卻胡侯、鄯善都尉、擊車師都尉、左右且渠、擊車師君各一人,譯長二人。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,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,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。地沙鹵,少田,寄田仰谷旁國。國出玉,多葭葦、檉柳、胡桐、白草。民隨畜牧逐水草,有驢馬,多橐駝,能作兵,與婼羌同。”
這是史書中最標準的介紹,離長安有多遠,離陽關多遠,多少戶人口,如何設置行政級別,水土如何,特產如何,都是實用的政治地理信息。在概述之后,漢書又用了幾頁的篇幅,介紹了樓蘭夾在漢王朝與匈奴之間的搖擺不定,武帝的征伐,以及一次改變樓蘭命運的宮變。在漢書有載之前,早在四千年前,古羅布淖爾人已在樓蘭這片土地上開墾生息,以挖空的胡楊木為船棺,以列木為幟,以耕種放牧為生。今日厲風吹蝕的沙海,當日卻是孔雀河流域,煙波浩渺、船只往來的沙漠綠洲。
還有精絕國,著名的“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討南羌”護臂就出土于尼雅遺址中的精絕王墓。當尼雅河水依舊能灌溉精絕時,這里的人們因扼守絲路南端上的咽喉,王侯貴族和僧侶們,過著相當奢靡的生活,著錦戴金,用著雕花的木桌,夏日里還能吃上冰鎮的葡萄,關于精絕國,漢書上的記載僅有百來字。公元四世紀城池廢棄后,它再一次被世人所知,是因為斯坦因的盜掘。
無論樓蘭還是精絕,其第一次被大規模盜掘都始于斯坦因之手。彼時位于清朝末期,政局動蕩,正是西方考古學家對中國西部文物展開一次次劫掠的“良機”。長達三十年的時間,從甘肅到新疆,大量文物被盜掘偷運到了西方,成全了一大批西方考古學家的“聲名”。他們的作為,是為了盡可能盜取更多的珍貴文物,“尋寶”手法粗暴,破壞了大量遺址地所存的珍貴考古信息。直到上世紀三十年代,當一大批中國新知識分子覺醒之后,學界和知識界聯合起來成立“古物研究所”與來自西方的盜掘者們展開對抗,這場劫掠才算到了尾聲,斯坦因最后一次造訪尼雅受到了嚴密監視,終于未能攜帶文物出境。樓蘭與精絕,一百多年考古史摻雜了中國的王朝變遷與時代動蕩,摻雜著屈辱、痛心、悲壯與覺醒。
一座綠洲因何而驟亡?消失的不僅是城市,還有河流和湖泊,胡楊和紅柳。在漫長歲月中進化出的脆弱平衡,因人類活動的增多而漸漸不堪其重。人類明知水源和樹木是沙漠里的生存之本,在兩千多年前就已頒下不許隨便砍伐樹木的法令,卻依舊難以經受眼前之利的誘惑。城頭變幻大王旗,漢家王朝打通的西域曾庇佑過這些綠洲的繁榮,但戰爭依舊難免。長風凄厲,人去城破,河水的尾閭不斷后退。那些城池的傳說漸漸隱去,最后變成史書上的百十個字。王治精絕城,去長安八千八二十里。戶四百八十,口三千三百六十,勝兵五百人。冷冰冰的記述,文字里沒有絲毫感情。
《懸念樓蘭-精絕》作者王炳華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生人,與樊錦詩基本同齡,是新中國成立之后培養的第一批考古學家。為著中國考古事業,躡先輩足跡,吃了許多人所不能之苦。中國西部干旱多風,白日酷暑而夜間絕寒。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曾書寫當年玄奘法師西行之苦———“乘危遠邁,杖策孤征。積雪晨飛,途間失地;驚砂夕起,空外迷天。萬里山川,撥煙霞而進影;百重寒暑,躡霜雨而前蹤。”行走其間,已是苦不堪言,王炳華為發掘尼雅遺址,在其中工作了整整九年之久。尼雅城破已一千六百年,早無水源,深埋塔克拉瑪干沙漠之中。在這種環境下工作,除意志堅忍之外,對考古事業的摯愛之情應是根本動力。猶如敦煌最初的守護者常書鴻、段文杰們,以身獻祭,工作于斯葬于斯,將生命獻祭給了輝煌的石窟寺文化。
大家寫小書,實是功德無量之舉。《懸念樓蘭-精絕》史料翔實、娓娓道來,條分縷析卻又文字芬芳,讀完書,如飲醇酒般痛快。我想起前兩年間輾轉于河西走廊,也曾目睹過破城瓜州鎖陽城,在附近的榆林窟,當地的研究員說,二十年前來此地尚不通自來水,河水是咸苦的。今時今日,普通人能將史書上的記載,與博物館中的實物對照起來細細品讀,能從數千年的維度來縱觀龐大的中國文明史,不禁生出萬分感恩之心。


 設為首頁
設為首頁
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
 聯系我們
聯系我們